這本書從醞釀到寫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80年代初,我產生了寫這本書的念頭,但促使我對延安整風這一事件萌發興趣則是在更久遠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觸到「延安整風」這個詞是在文革爆發前夕的1966年春。記得有一位前輩學者曾說過,舊中國黑暗的現實,使中國的青少年比歐美國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趨於早熟。我想說的是不僅在舊中國情況如此,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情況亦是這樣。新中國層出不窮的政治鬥爭及其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使我不幸地過早地關注起自己不應該去關心的事情。
我讀書啓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個政治意識畸形發展的年代。從1963年初開始,我對母親訂閱的《參考消息》發生了興趣,經常躲着她偷偷閱讀。我也從那時起,養成了每天讀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的習慣。可是我對那時的社會狀況並不清楚—應該說,除了雷鋒、革命先烈、越南、紅軍長征的故事,那時我的頭腦中並沒有任何其他東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我愈來愈注意《參考消息》和報紙上刊載的有關中蘇兩黨論戰的報道。1964年春夏之間,我從《人民日報》上看到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蘇共二月全會上作的「反華報告」,第一次看到對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這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震動(這份報告給我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以後我長期保留這份《人民日報》)。我開始思考蘇斯洛夫報告中所論及的一些詞彙:毛澤東是「左傾冒險主義」、「半托洛茨基主義」、「唯意志論」等等(七十年代,我從內部讀物才知道,蘇斯洛夫是一個頑固的教條主義者。近年出版的俄羅斯資料透露,1964年蘇共黨內的革新勢力利用與中共的論戰,削弱了斯大林主義者在蘇聯的陣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勢力復辟的勢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保守的蘇斯洛夫才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作了這個報告)。對於這些話,當時我似懂非懂。我聯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幾年前那些飢餓的日子,我隨母親去南京郊外的勞改農場去探望因「右派」問題而被下放勞動的父親,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語學校錄取,卻因政審不通過而被拒之門外—我對當時的政策居然產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連小學也講起「階級路線」,我因出身問題越來越感到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迎來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學校的號召下,我通讀了《毛選》1至4卷,我多次閱讀了收入《毛選》中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毛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於是我知道了「整風運動」這個詞。
緊接着文革爆發,我從每天讀的《新華日報》上發現,1966年5月初北京召開的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羣衆大會上不見了彭真的名字,接下來我就讀小學的一些幹部子弟(我的小學鄰近南京軍區後勤部家屬大院和《新華日報》社家屬區),手拎紅白相間的的體操棒在操場上毆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歲的余姓美術教師,校長兼支部書記則裝着什麼也沒看見。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紅色恐怖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衝擊,有一天,我無意中父母的談話,父親說,這一次可能躲不過去了,再不跑,可能會被活活打死。父親終於離家出逃,躲在山東農村老家那些純樸的鄉親中避難,不久,我家附近到處貼滿了父親單位捉拿他的「通緝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幾何時,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揮揪鬥「死老虎」的當權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馬,「周揚四條漢子」、「彭羅陸楊」、「劉鄧陶」像走馬燈似地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頂頂皇冠落地」!從那時起,我就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報紙上的「排名學」。1967年初,在南京大學的操場上,我親眼看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被批鬥,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學的校長還是滿口「江政委」喚個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辦公大樓,那裏正舉辦所謂「修正主義老爺腐朽生活」的展覽,那寬大的帶衛生間和休息室的書記辦公室,那嵌在舞廳天花板壁槽內的柔和燈光,以及用從緬甸進口的柚木製成的地板,無一不使我頭腦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參加這場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從各種書籍中所獲得的精神營養也使我不會去欣賞那些在革命名義下所幹的種種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個區文化館圖書室的借書證,因此我讀過不少中外文學,歷史讀物。至今我還記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從母親的手中奪下她正準備燒掉的那套楊絳翻譯的勒薩日著的《吉爾·布拉斯》等十幾本書籍。在焚書烈火中被搶救下來的《吉爾·布拉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普希金詩選、《唐詩三百首》等給了我多少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飄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長江路南北貨商店牆上看到一張「特大喜訊」的大字報,上面赫然寫着葉劍英元帥最近的一次講話,他說,我們偉大領袖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毛主席可以活到150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頭腦轟地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了。我馬上去找我的好友賀軍—他目前住在美國的波士頓,告訴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爲,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歲,因爲這違反科學常識。
從這時起,我在心裏悄悄地對毛澤東有了疑問。我知道在中國,一切都憑他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即使劉少奇,雖然《歷史決議》對他評價極高,雖然在文革前到處都能看到毛、劉並列的領袖標準像,雖然劉少奇夫婦訪問東南亞是何等的熱烈和風光,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喜歡,劉少奇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邊發生的一些事,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小巷的破矮平房裏,住着與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對姐弟和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媽媽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在街道煤球廠砸煤基(蜂窩煤)。因爲不能忍受歧視和侮辱,這位母親竟失去控制,將毛主席的畫像撕碎並呼喊「反動口號」,結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槍斃。召開公判大會那一天,我的中學將所有學生拉到路邊,觀看行刑車隊通過,美其名曰「接受教育」,這姐弟兩人也被安排在人羣中,親眼目睹他們的母親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車隊通過後,學校革委會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組討論,於是所有同學都表態擁護「鎮壓反革命」—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對毛產生了看法。我知道這些看法絕不能和任何人講,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講,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歲月裏,沒有希望,沒有綠色,除了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賀軍,差不多也沒有任何可以與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們之間的談話也小心翼翼,絕不敢議論毛澤東),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線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學留守處,這個中學已被勒令搬至農村,所有被封存的圖書都堆放在留守處的大倉庫裏,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東人,年青時被國民黨拉去當兵,被解放軍俘虜後成爲「解放」戰士)。至今我仍感激這位老先生,是他允許我每週進一次倉庫借一旅行袋的書,下週依時交換。正是在那裏,我翻檢到1958年的《文藝報》的《再批判》專輯,因而我第一次讀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那幾年,我從這個倉庫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學和歷史書籍,至今還記得,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葉集》、葉聖陶的《倪煥之》、老舍的《駱駝祥子》,就是在那個時候讀的。1971年後南京圖書館局部恢復開放,我又在每個休息日去那裏讀《魯迅全集》,將包括魯迅譯著在內的舊版《魯迅全集》全部通讀了一遍。正是這些作品支撐起我的人文主義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國內的政治局勢更加險惡,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憤恨江青的專橫,在1975年從其位於南京市衛巷家中的閣樓上跳下自殺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組老太太的監視,只要家裏來一外人,她就站在門口探頭探腦,東張西望。197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與好友賀軍坐在長江路人行道的路邊,我背誦了魯迅的話:「地下火在運行,岩漿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與賀軍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園坐了半天,我們共同回憶起往昔歲月,我們都談到1976年夏在長江路邊的那次談話)。
在文革期間,我讀了許多毛的內部講話和有關「兩條路線鬥爭」的資料,這些資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謊言,然而它們還是激起了我強烈的興趣。結合文革中所發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願望,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風運動—這雖然是距那時以前幾十年的往事,但我還是隱約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與它有聯繫。在大字報和各種文革材料中,我難道不是經常讀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長」的講話嗎:什麼「×××最壞,在寧都會議上,他想槍斃我」,「劉少奇在抗戰期間勾結王明反對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什麼「×××在延安審幹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對他控制使用」,還有「王明化名馬馬維奇在蘇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裏,我雖然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卻不知填了多少表格,從小學、中學到工作單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會關係」欄內填寫老一套的內容。看看周圍的人,大家也一樣要填表。我工作單位的人事幹事是從老解放區來的,她說,這是黨的審幹的傳統,是從延安整風開始執行和推廣的,那麼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帶着這些疑問,1978年秋,我以歷史系作爲自己的第一選擇,考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1979年後的中國大學教育開始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經歷了那幾年由思想解放運動而帶來的震撼並引發了更多的思考。在課堂上,我再次聽老師講延安整風運動,我也陸續看到一些談論「搶救」運動的材料,然而所有這些都在維持一個基本解釋: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1979年我還讀到周揚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將延安整風與五四運動、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謂之爲「思想解放運動」。在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知道,雖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被批評,但毛的極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滲透到當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成爲某種習慣性思維,表現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甚行,爲聖人避諱,或研究爲某種權威著述作註腳,幾乎成爲一種流行的風尚。當然我十分理解前輩學者的矛盾和苦衷,他們或被過去的極左搞怕了,或是因爲年輕時受到的《聯共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思想訓練太深,以至根本無法跳出官學的窠臼。
然而,我難以忘懷過去歲月留下的精神記憶,劉知幾雲,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我難以忘記1979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所引起的激動,我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所有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條的束縛,努力發揮出自己的主體意識,讓思想真正自由起來。從那時起,我萌生一個願望,將來要寫一本真實反映延安整風的史書,爲此我開始蒐集資料。
由於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在80年代以後,中國也陸續披露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料,除了少量檔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強了我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
經過對多年蒐集、積累資料的反覆研究和體會,我頭腦中的延安整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我開始發現散亂在各種零碎資料之間的有機聯繫。1991年8月中旬我開始動筆,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從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寫作速度慢了下來,一則日常教學工作十分繁重,牽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則我需要更廣泛地蒐集、閱讀各種資料。
1995年夏— 1996年秋,我有機會去設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作訪問學者,我在美國的研究題目與延安整風無關,但我仍利用在華盛頓的機會,在國會圖書館工作了一個月。但是很遺憾,國會圖書館中文部雖然收藏十分豐富,但是幾乎找不到有關延安整風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國後,又重新開始寫作,到了1998年夏,全書已經完成。我又用半年時間對書稿作了3次修改補充,於1998年底,全書殺青。1999年初交稿後,在編輯校對階段,我接觸到若干新材料,對書中的個別內容再次做了充實,於1999年春夏之交,全書最後定稿。
我寫這本書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實爲依歸,在寫作過程中,始終遵循據事言理的治學方法。我以爲,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爲數十年意識形態的解釋學早將當年那場事件搞得雲環霧繞,面目不清。爲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對各種重要和非重要的資料進行點滴歸攏,爬梳鑑別,再對之反覆研究體會,使之融匯貫通。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我不反對對延安整風這一重大現象進行嚴謹的理論分析,且認爲,這個工作極爲重要,但是我又擔心過度解釋而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陳寅恪先生言,「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滴水觀滄海」,因此在本書中,我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論述的方式展開,這也與我個人比較重視歷史的個案研究有關。
在寫作此書的7年裏,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衆所周知,有關延安整風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社部、中組部的檔案文獻,除少量披露外,絕大部分迄今仍未公開。1992年,我看到一位負責人在中央檔案館的講話,他說,鑑於蘇東鉅變的深刻的歷史教訓,應該加強對檔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他指出,中共檔案資料的保管,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我可以理解這位負責人的觀點,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卻爲不能閱讀利用這些珍貴史料而感到無窮的遺憾。
由於這是一本站在民間立場的個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裏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項目的資助,我知道,即使申請也不會成功。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
最後,我的遺憾是我應該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90年代後,莫斯科開禁歷史檔案,涉及40年代蘇共與中共交往的文獻記錄也已開放。中國歷史學會的沈志華博士近年來爲蒐集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並已將其中某些材料轉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訴我,蘇共與中共在延安整風期間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國,一時聯繫不上,這也使我深感遺憾。
伏案几載,每天神遊於當年的歷史景像之中,自然會對延安整風運動及其相關的史事與人物產生種種體會,這方面的體會與感受的絕大部分已化爲書中的敘述,但是還有幾點需在此予以說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創革命的年代。吾細讀歷史,站在20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共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爲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
2、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所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已逐步走出過去那種懷疑一切,無情鬥爭的極左道路,但舊習慣思維的清理仍需長期努力。吾期盼舊時極左的「以我劃線」、權謀政治永不再來,國家從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軌道,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書涵蓋面頗寬,涉及中國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對於本書所論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將其看成歷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惡偏見,主觀上力求客觀公允,「不虛美,不隱惡」。當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價值關懷,陳衡哲先生曾說過,「若僅縷述某人某國於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麼意思」,說的也是研究者的價值關懷問題,只是這種價值關懷不應妨害到敘述的中立和客觀。如果說本書敘述中有什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爲然的五四以後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裏,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寶貴的支持和鼓勵,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謹向他們表示真摯的感謝。
上海師範大學的許紀霖教授多年來一直關心我研究的進展,他還熱情的爲本書的出版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在與許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學養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卓越見解總是使我深獲教益。
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教授和劉青峰教授。他們對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在本書定稿過程中,他們提出一些富有啓迪性的建議和意見,對於本書臻於學術規範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學歷史系顏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現旅居美國的賀軍先生表達我的感激,他們的友誼和支持,對於我一直是一個激勵。
我曾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問題研究院「華盛頓—南京辦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Kane)有過多次關於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黨史問題的愉快的討論,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對於我的寫作是一種推動。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裏,我始終得到我過去的學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關心和幫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對我幫助尤大,他不僅幫我用電腦輸入文字,還與我分享了討論的樂趣,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我也向本書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編者表示我的謝意,我雖然在引述文字時都做有詳細的註釋,但沒有他們提供的資料基礎,我要完成這本書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書的編輯鄭會欣博士表達我深深的謝意,鄭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務,但是他還是撥冗爲本書做了許多瑣細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對本書的出版有重要的幫助。
1998年夏秋之際,我有機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訪問研究,在「大學服務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在這個收藏豐富的史料中心,我爲本書補充了若干新的資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學服務中心」表示謝意。
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的老師們多年來在圖書資料方面給了我許多幫助,對他們的友好、善意和敬業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後,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妻子劉韶洪和兒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餘,承擔了大量的家務,使我可以專心致志進行研究,她還爲書稿作了一部分的電腦輸入工作。爲了寫作這本書,許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遊玩,也不能與孩子經常討論他的功課,沒有他們的支持、幫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書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於南京大學
(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書60萬字)
附該書目錄:
前言
上編: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1、$$%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專政$$%問題2、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爲與中共中央的反應3、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5、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6、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第二章: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與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1、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2、從毛、�牛ㄎ盤歟┝說矯⒘酰ㄉ倨嬀┝?、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4、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1、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和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2、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3、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4、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第四章:毛澤東對王明的初步勝利
1、毛澤東迂迴反擊王明2、關於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爲中共領袖的$$%口信$$%3、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4、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五章: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1、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麼?2、$$%挖牆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3、$$%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下編: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及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2、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3、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4、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5、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雲、李富春6、扶植地方實力派:毛澤東與高崗7、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處境尷尬的軍方
第七章: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1、窮途末路的國際派2、進退失據的周恩來3、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第八章: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1、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麼?2、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第九章從$$%延安之春$$%到鬥爭王實味
1、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2、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3、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刀4、毛澤東爲什麼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5、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幹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1、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2、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3、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4、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第十一章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幹
1、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2、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3、審查在後: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4、爲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後活動5、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6、$$%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盪靈魂7、$$%得救$$%:$$%新人$$%的誕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幹、反奸與搶救運動
1、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託$$%2、1940年的審幹與幹部檔案制度的建立3、$$%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反奸(肅反)$$%4、毛澤東的$$%肅反$$%情結:從$$%肅AB團$$%、$$%肅託$$%到$$%搶救$$%5、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係6、在$$%試驗田$$%裏創造出的$$%張克勤案$$%7、$$%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第十三章 $$%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1、$$%搶救$$%的策略和手段2、中直機關的$$%搶救$$%3、軍直機關的$$%搶救$$%4、西北局和邊區系統的$$%搶救$$%5、中央黨校的$$%搶救$$%6、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搶救$$%7、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8、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9、華中根據地的$$%搶救$$%10、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第十四章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1、$$%審幹九條$$%再頒佈後,$$%搶救$$%爲什麼愈演愈烈?2、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4、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第十五章、$$%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1、$$%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2、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3、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4、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爲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5、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開檢討6、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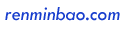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