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两点,高士功照常去上中班。许多小青年上班来点个卯就没影了,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去天安门了。北京城这两个月火红的日子,就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有哪个不动心,哪个不神往?高士功是党员班长,习惯了以身做则,别人尽可以溜号,他却不能走也不想走。吃晚饭的时候,厂内大喇叭里广播市政府公告,要“市民呆在家里,别出门”。老高心里有点打鼓,他是不放心家里十六七、二十出头的三个大秃小子。老高家住呼家楼,头些日子他在家门口看到了市民拦截戒严部队的油罐子车,双方也没咋著。入伍几年的“拥军爱民”教育,又使老高确信军队不会动“真家伙”。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北京第一机床厂出动的工人民兵,棒子都没拿,就把“暴徒”架离了天安门广场,还立了集体二等功。后来,“四五运动”案翻过来了,弄得立功的人灰头土脸,成了大伙儿的笑料。
晚十点高士功下班,一出厂门就觉得街上气氛不对。机床厂出门就是建外大街,直达长安街,素称“中华第一街”。街上布满路障,到处都是人;有说戒严部队一辆装甲车强行突进压死人了,装甲车在建国门桥上还挑翻了部队自己的一辆带棚卡车。高士功心中惦著孩子,赶紧骑车回家。到家一看,仨秃小子少了一个,不用说,准是去了天安门。老高回身蹬车就往长安街骑,去找孩子。
高士功刚过北京饭店就听到了枪声,此时到处都是人流,有退的有进的,还有的喊发射橡皮子弹了。枪子是从西边打来的,又一阵枪声响起,有人中弹倒下,老高转脸一看,动真枪实弹了!高士功惊讶得“啊”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老高张开嘴“啊”的瞬间,一粒子弹从老高脸颊洞穿而过,自左脸颊打进右脸颊穿出,鲜血顿时流了下来。惊悸中的老高捂著伤口不顾一切地随著人流奔逃,只恨自己入伍干的是伙头兵,从没学过紧急撤退时的战术战法。
六四大屠杀过后,凡是外伤的住院者,都要经公安部门的逐个审查,以清查“暴徒”。高士功住进了北京医院。据医生讲,多亏高士功“啊”了一声,张圆了嘴巴让子弹在薄薄的双颊顺利穿过,否则下巴就会被打烂;苍天有眼,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临出院受公安审查、提问,单位给老高说好话:“这个老工人,历史太简单,是个老党员,思想很平凡。进厂学徒,征兵入伍,复员回厂。干在一线,没离开过大刨床。从不多说多道,人也太老实”。精明的公安一问话立马就看出这是个“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主儿”,放他去了。不过高士功得自负医药费,单位不管。上边有指示,没有“误伤”这么一说,“谁叫你上街赶著找著挨枪子来的”,还给领导添麻烦,以示惩戒。
高士功伤愈后第一次照镜子就呆住了。脸蛋上一边是“枣核”,一边是“涡旋”,一颗子弹“巧夺天功”,竟成就了两旋纠结对称的酒窝,近看是惊奇的笑意,远看是深深的笑靥;镜子里的人冲著自己只有一个表情:笑、笑、笑。挣不脱,抹不去,做不掉;一幅凝固的、强迫的、永久的笑。脸是表达感情的,他的脸将只显示一种感情。笑是人世间多美好的感情,而他的笑并非心声,却是苦涩、痛心、羞耻、不堪回首。他用双手捂住那两个人造的酒窝,还原爹妈给的天然脸,依旧平实、诚挚;放下手,素面朝天已永劫不复。
生活中的麻烦接踵而至。他的家人,老伴、儿子,再也不会面对他笑了。因为笑已成了他们全家的大忌,成了家庭最深的伤痕。高士功走在大街上,常有素不相识的行人冲他巧笑,因为行人以为他在向人家讨笑,投桃报李。邻居的孩子喊他:“高伯伯”,总不忘带上一句“高伯伯老笑”!单位里的同事、徒弟,远远望见他便会条件反射地向他微笑;五千人的大厂每个角落都流传著他被戒严部队的子弹打成两个酒窝、一幅笑脸的笑话。他去饭厅打饭,感觉到被人指指点点,彷佛有许多人禁不住偷偷地哑然失笑。他因脸上僵硬的笑而被无数的嘲笑、冷笑、暗笑包围著,这无数的笑如万箭攒心,令他心神疲惫、沮丧、尊严扫地。他辞去了班长,只是拚命地干活,话更少了。
有笑的日子是漫长的。高士功再也不照镜子了,他怀疑身边所有的笑,怕成为别人的笑料;笑,成了生活中无法控制的永久的威胁。他连发怒也做不成,因为脸上只有一种固定的表情。他开始羡慕那些破相的人,甚么刀疤、抓痕、缝合钩,随便烙在脸上甚么地方,也不影响表情达意,也能抒发七情六欲,有笑意就会呈现,有愤怒就能张扬。他感觉自己是孤独世界的人,幸福的来源已被破坏,感情已被埋葬。秋冬季节,他常常戴著大口罩,脸不示人。他盼著退休,躲避尘世。
高士功退休了。高士功有了孙子。当他第一次抱起孙子时,老泪纵横,全家人都知道当爷爷的心里在笑。可是他脸上的笑纹肌已经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摧毁了,凝固了,他已经永远不会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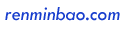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