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发行。为保存史料价值,对本书全文、作者前言和原编者约瑟夫·科辛斯基所作的注解和后记,均未作改动。谨供关注与研究苏联历史和现状、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读者以及有关领导阅读、参考。
前 言
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写此书也不是为要达到任何狭隘的政治目的。我唯一的意图,是把斯大林的“肃反”秘史公诸于世。为此,我将再现这一大事件中一系列关键环节,没有了这些环节的披露,这场大悲剧,就将成为永世不解之谜。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还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员。苏联政府曾先后让我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我曾积极地参与过国内,在西南战场的红军部队里奋勇作战,在那里我还指挥过敌后游击队,还负责过反特工作。
内战结束后。党中央任命我为最高法院副总检察长。顺便提提。我在那时参加过苏维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副主任。任务是代表国家监督苏维埃工业的改造和打击贪污受贿。后来,我被派往外高加索,指挥一支边防部队,负责保卫跟伊朗和土耳其接壤的边界。
一九三六年。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经济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负责外贸工作。
一九三六年,爆发了著名的西班牙内战。政治局派我去那里担任共和国政府顾问,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发展敌后游击战。我干一九三六年九月到达西班牙,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与斯大林政权决裂的那一天。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职期间,我成功地收集到了许多绝密材料,尔后又带到了国外。这些材料涉及斯大林为独揽大权而作的罪行;涉及一系列由他组织的、旨在清洗十月革命领袖们的审判;涉及他同那些受他迫害而死的人的关系。
我还记录了许多材料: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口头指示;发给侦讯人员的有关粉碎列宁老战友的反抗和迫使这些人作假口供的指示;斯大林与个别成了他的牺牲品的人的谈话,以及这些必死之人在卢比扬卡高墙内说的话。这些严禁外传的绝密材料,是我从内务部的一些侦讯人员手中得到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在我手下工作过。其中有曾是我助手米隆诺夫(后来是内务部经济局局长,为斯大林准备所谓莫斯科审判的主要帮手之一)和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
在整个非法活动中,斯大林不可能没有内务部的忠实助手。随着他的暴行的增加、他的同谋者也就越来越多。斯大林害怕自己在世人面前名声扫地,决心在一九三七年除掉所有亲信,使其永远不能成为他的罪行见证人,一九三七年春,内务部里绝大多数领导人,以及那些按他的直接指示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人、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大搞刑讯逼供的侦讯人员,统统未经侦查和审判便被枪决了,此后,上千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又相继销声匿迹:这些人在内务部工作过,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关斯大林罪行的绝密材料。
我是在西班牙得知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被捕的。紧接着,我的老朋友和同年—一被杀害的消息又传到我耳里,看来,马上就该轮到我了。然而,我不能与斯大林制度公开决裂。我的母亲还住在莫斯科,按斯大林那些野蛮的法律规定,她实际上是当权者扣下的人质。一旦我拒绝返回苏联。她就可能被处死,我妻子的母亲也将处于同样的境地。
在西班牙战场上,特别是在火线组织共和国军队进攻时,我常常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在这种时候,我多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我在执行任务时被打死,那么我的家庭以及我那些留在莫斯科的好友所受到的威胁,马上就会解除。这种憧憬对我来说。远比公开与莫斯科决裂更有吸引力。
但这是软弱的表现。我继续在西班牙人中间工作,他们的英勇无畏常令我赞叹不已。同时,我头脑中还存在一个幻想:说不定,斯大林会死在某个同谋者手中。或者,莫斯科那场恶梦般的“清洗”,会突然间自行停止。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收到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的一份电报。电报说,佛朗哥和德国希特勒的特务组织正在制订计划,企图将我绑架出西班牙,以便从我口中掏出有关苏联援助西班牙的规模的情报。
斯卢茨基还通知说,内务部打算派一个十二人的卫队来保护我的安全,他们将时刻不离我左右,我顿时意识到,这个“私人卫队”的首要任务是来除掉我本人。于是我电告斯卢兹基,说我用不着私人卫队。因为我的司令部昼夜都有西班牙的“国民近卫军”守卫,而且,一出司令部就有西班牙秘密警察局的武装便衣特务护卫。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样,内务部就没给我派什么私人卫队,但这件事却使我警惕起来。我开始怀疑叶若夫这个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已给自己的秘密“别动队”下令,要把我杀死在西班牙。预料到这一点后,我就派了一个参谋前往正在前线作战的德国国际支队,要他们挑选十名可靠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给我送来。从此,这些手提自动枪、腰挂手榴弹的战士就寸步不离地一直跟随在我身边。
一九三七年十月,斯卢茨基的副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来到了西班牙。三个月前,正是他在瑞士组织暗杀了拒绝回莫斯科的内务部情报站站长伊格纳季·莱斯。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的妻子和女儿都还在苏联,实际上就是人质,因此他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太乐观,说不定,也在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但这也绝对不会使他变得不那么凶险。西班牙并没什么事非要他来办不可,所以他的到来只能加深我的怀疑,尤其是我后来得知,他曾在马德里与某个姓鲍罗金的人碰过头。而那个鲍罗金是叶若夫派到西班牙来领导“别动队“进行恐怖活动的。
什度格尔格利亚斯和鲍罗金肯定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专门的卫队保护,要想暗杀我,难免发生枪战。那样,双方就会死伤惨重,谁也占不到便宜。所以我想,莫斯科会不会命令鲍罗金绑架我那十四岁的女儿,然后再恫吓我,逼我回苏联呢?这可怕的念头死死地缠住我,迫使我火速赶往郊外我妻子和女儿住的地方,用汽车将她们送到了法国境内。我在那里为她们租了一座小别墅,离西班牙边境不远,并把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配给我的忠实保镖兼司机留在她们身边,而我则又回到了巴塞罗那。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推迟与莫斯科决裂的时间,因为我明白,这样做同时是在延长我母亲和岳母的生命。
我一直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会发生什么事变,彻底结束那无休无止的恐怖恶梦。
最后,是莫斯科自己决定了我的命运。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叶若夫的电报。此人当时已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他命令我前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并于七月十四四日登上停泊在那儿的苏联舰艇“斯维利”号,与一个“您很熟悉的同志”见面。同时还指出,我前往那里时,必须乘坐我们驻巴黎使馆的汽车,并由苏联驻法国总领事比留柯夫陪同:“鉴于所面临的任务十分重要,此人作为联络员是非常适宜的”。
电文很长,很罗嗦。叶若夫及其随从,都是才从中央机关调到内务部的,与现在被镇压了的原内务部头头们相比,显得太没经验。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这些人挖空心思,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企图。毋庸置疑,“斯维利”号舰艇将是我的浮动监狱:我的回电是;将于约定之日到达安特卫普”。
七月十二日,同事们纷纷聚集在巴塞罗那的官邱旁,与我告别。我觉得,他们都知道我将走向陷井,而且深信我会掉进去。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便到达法国边境。辞别了卫队和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那位与我形影不离的便衣后,我就由西班牙司机送到了佩皮尼扬市的一间旅社,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我。接着,我们坐上一趟夜间的特快列车,次日凌晨便到了巴黎。这下,我顿时觉得自己仿佛从沉没的轮船上脱了险,而且是那么出乎意料,既没预先准备,也没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内务部在法国的间谍网极为严密,不出两天,叶若夫的特务就会找到我的踪迹。这就是说,我必须尽快逃离法国。
“对我来说,唯一安全的避难之处是美国。我给美国大使馆挂了电话,请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电话。但当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前一天,使馆的人回答我,说大使不在。于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议:找加拿大代办处去。在那里,我出示了外交护照,并申请去加拿大的签证,借口是想把家属送往魁北克度夏。
苏联与加拿大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我很担心加拿大代办处拒绝我的请求。但这位曾担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长的代办处负责人很同情我们。他主动以自己的名义给魁北克的移民官员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给我以帮助。一并把信交给了我。同时,我们又在代办处大楼里碰上了一位牧师。他与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说,加拿大的“蒙克利尔”号轮船恰好今天要从瑟堡起航,而且还有几个空位。我急忙赶往船票代办处,妻子则直奔旅社去接女儿。当我们三人赶到火车站时,火车正好要开动。几小时后,我们便顺利地登上了轮船。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离开了欧洲。
我的女儿是轻松愉快地踏上这次旅途的。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晓得该如何向她解释,要知道,她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伙伴、两个奶奶和祖国。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时间都生活在国外,而女儿对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从没蒙上过丝毫阴影。由于急风湿关节炎。她很少有机会观察到现实生活,所以根本不了解祖国同胞的深重苦难,更别说斯大林政权的残忍了。我和妻子从不想打破她的各种美丽的幻想。女儿从小就特别憎恶任何粗暴的行为,同时,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们知道。由于风湿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暂,因此尽量不让她知道真情,当然,这个真情是指斯大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罗斯人民的悲惨命运。
很难向她解释我们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还是明白了。她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哭得十分伤心。她心月中那个理想世界,到头来竟是一片虚幻,过去那些美丽的幻想。统统变成了泡影。她曾为父母在国内战争中出生入死地战斗过而自豪,可现在,却为我们而痛苦。一夜之间,她长大成人了。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覆写件同时寄给了叶若夫。在信中,我向从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认识的斯大林谈到自己对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于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们的两位母亲的性命。我知道,恳求斯大林不对她们下毒手,唤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一种适合对付斯大林的办法。我鼓足全部勇气,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恶气出在我母亲的身上,那我就将他的一切罪行公立于世。为了证明这不是拿空话来吓唬他,我特地拟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单附在信后。
除此之外,我还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务杀害,我的律师也会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于我深知斯大林的为人,所以我确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视为儿戏。
我卷入了一场赌博,一场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赌博。但我坚信。斯大林肯定会推迟对我的报复。在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没把我绑架住,没逼我交出秘录之前,他是不敢下手报复的,当然,他会不遗余力地满足自己的复仇欲,但这只能在他坚信自己的罪行永远不会暴露之后。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离西班牙一个月之后,我带着美国驻渥太华代办处负责人给的入境签证,抵达了美利坚合众国。
到了美国,我立即带着律师前往华盛顿。我向那里的移民局局长递交了声明,宣布与自己祖国的政府脱离关系,并申请政治庇护。
另一方面,斯大标对我的追杀马上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了十四年。在这场较量中,斯大林既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又动用了大批秘密特务。而我这一方,则仅靠自己的远见和识别陷阱的能力,以及我的亲人,即妻子和女儿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来应付。
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给我俩的母亲以及在苏联的朋友写信,以免他们的生命受到危害。对他们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
一九五三年初,我和妻子都断定母亲已不在人世,所以决定将这本书拿去发表。二月里,我开始与《生活》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洽商,淮备发表某些章节。可就在商谈之时,斯大林死了。我十分扫兴,为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时候,那样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于世,就会认识到为自己隐瞒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
斯大林之死,并不意味着我一辈子从此既突然无恙了。克里姆林宫为着保住自己的秘密,仍将不遗余力地找我算帐,哪怕仅仅是为了警诚那些想效法我的人。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一九五二年六月,于纽约
注解:
①尼·伊·叶若夫(一八九四——一九三九?)苏联共产党高级官员,历任州党委书记.苏联土地部副人民委员、党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十七大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工业部部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运输部人民委员,一九三大年九月接替亚果达兼任内务部人民委员,组织实施了被称为“叶吉夫恐怖”的大清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一九三九年被捕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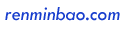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