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飘萍当年,不以任何特殊的权势集团为后盾,仅凭一支笔,以极为有限的资金,个人独资创办《京报》。时在1918年10月5日,正值“五四”新思潮澎湃之际,“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他的办报宗旨,“铁肩辣手”是他的座右铭,他为新闻报国的理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新京报》表示“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这个传统究竟是什么?首先就是民间办报,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不听命于军阀、官僚或者外国势力,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从《京报》到《大公报》《新民报》等都是如此,也就是要有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性,才能坚持公正报道、独立发言。其次是文人论政,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完全从良心、道义立场出发,不受制于其他外在力量,绝不以办报作为进身之阶,仕途的敲门砖,始终与权势者保持距离,做社会良知。从邵飘萍、林白水到史量才,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报业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无论那时的军阀多么贪婪、社会多么昏暗,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邵飘萍生前可以藐视军阀当道,以监督政府的民众喉舌自任,在他自办的《京报》笔扫千军。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敢于把“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作为《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新京报》生不逢时,遭遇了一个自由“有”还是“无”、连打擦边球也风险莫测的时代,君不见《21世纪环球报道》前车之鉴,要想存在下去,除了向现实低头,几乎很难有其他的出路。《新京报》本身就是两家党报集团合办的(“不党”、“不卖”根本就没有可能),头上悬著中宣部的利剑,条条禁令之下,要想有所发展也无非通过版面的花色翻新招徕读者、取悦读者,做些无关痛痒的新闻,说些不著边际的风凉话,来点吃喝玩乐、风花雪月,“不私”、“不盲”更无从谈起。
当然,这才是正常的。假如真的像《新京报》所标榜的,以“负责报道一切”作为报道理念,这张报纸恐怕办不了几天就只好夭折了。“负责报道一切”,好大的口气,你能报道高层权力运作的内幕吗?你能发出对“神五”上天的不同声音吗?你能对好大喜功的三峡工程说不吗?你能如实报道让亿万百姓深恶痛绝的不公平拆迁吗?……在新闻自由没有到达中国之前,这只能是一句空话。任何承诺都需要担当,明知兑现不了仍要宣扬,不是虚伪,就是欺骗。什么是担当?还是看看邵飘萍吧,即使生命危在旦夕,他在《京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依然是嬉笑怒骂、从容不迫。今天已没有那样的环境,这可真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啊。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新京报》的理想何其动人,就算把这些话当做邵飘萍办《京报》的宗旨,恐怕也不会有争议。然而它忘了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还有一个高于一切的党的利益,即便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本真,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丑恶,什么是公义,所有这些都是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党来确定的,作为两家党报集团的子报,《新京报》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可能在早已划定的圆圈外动脑筋。“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注定了此路不通,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都抵挡不了普天之下莫敢不从的宣传纪律。邵飘萍以一死成全了《京报》的报格,时至今日,放眼神州,早已没有民间报纸的容身之处,《新京报》和《京报》只不过是两个表面相同的词汇,骨子里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精神追求,呜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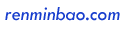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