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放亮了。当田鼠、野兔、家犬和耕牛都挺著大肚子,晃荡著腹水从我们的观察哨前蹒跚而过时,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血防”垮了──
兽犹如此,人何以堪。
血吸虫,一个湿漉漉的夜行性噩梦,当我们议论它“回潮”,诧异它“死灰复燃”时,它笑了:它根本就没有被消灭过。
在湘鄂赣疫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它只是被伟大的诗歌消灭过。一如当年一首民歌就可以使我们的粮食亩产万斤一样,它也只是被两首最杰出的诗“送走”了而已。
“瘟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湘、鄂、赣大地。当我们匆匆宣布全国300多个流行县中141个达到完全消灭血吸虫标准,122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因而“中央血防领导小组”也从上海北撤时,“瘟神”笑了。
它不但继续威胁著“1亿人口”,而且把“基层血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标志性机构”也送走了……
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肖东楼于2003年9月28日坦承:中国血吸虫疫区钉螺明显扩散,新疫区不断增加并向城市蔓延,血防形势“异常严峻”。
疫情如炽,“千村薜荔人遗矢”的场景还会重现吗
所谓“八百里洞庭疫水包围沿湖四百万生灵”的报道,并非危言耸听。
14年前的1989年,我曾经赴疫区采访,14年后重返疫区,发现疫情不但依然“如炽”,而且连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也基本崩溃。
一份资料显示,湖南省现有血吸虫病人21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洞庭湖区现在光病畜就有5万头,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现有钉螺分布面积的52%。且泥沙淤积,洲土不断扩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积还以60万公顷至90万公顷的速度增长。
湖南益阳市是血吸虫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7个县中有5个是灾区,全市500多万人中,120万曾经或者正在遭受血吸虫病的折磨,其下属的沅江地区地处洞庭湖中心地带,现有血吸虫病人4万,晚期血吸虫病人(简称“晚血病人”)1400余人,属于疫区“大户”,走进沿湖村落,家家都有吃药的。
陪同我的血防干部说,说人的悲惨故事我都乏了,还是看看动物多悲惨吧。
9月24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在沅江市漉湖苇场3号观察点用望远镜观察洲滩沼地边活动的动物。
两只野犬的奔跑姿势已经走样,像“软脚蟹”一样,它们的背部瘦得凹陷了下去,像一根铁轨,肋骨历历可数,肚子大而且晃荡,几乎触及草皮,乍一看还以为是超常怀孕的母犬,苇场的已经感染了血吸虫的渔民顾有财说,那是晚期腹水,我们叫“晚血狗子”,活不了多久了。
来自安徽的顾有财,身后跟著3个“血孩子”,依次为10岁、8岁、7岁,和顾有财一样,个个面黄肌瘦,都是今年高温期间沾水感染的,“政府要我们别下水,他们给吃的?没办法,不下去捞鱼,一家五口吃什么?”他说,我老婆也感染了,躺在船上起不来。湖荡里,像我们这样全家感染的外乡渔民有几百户!
一群大肚子的“晚血”沟鼠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懒洋洋地逡巡,肢体柴瘠,目光散乱,动作蹒跚,完全丧失了鼠类应有的敏捷和狡黠,甚至见人吆喝也不躲。
最令人不忍的是“晚血”耕牛,劳作了一辈子,现在也“肚子大了”,两肋瘦成了真正的牛排,肚子却胀得像个热气球,肉眼就可以看到它的肚子上青筋暴绽,晃荡著走不多远就躺在沼地上喘息,两眼绝望地望著人们。
同村的早就鼓动主人宰了它,主人不忍,遂成了这样的牛骷髅。
益阳市血防办副主任杨解庭说,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可以受到血吸虫病的攻击,部分动物有自愈能力。有阳性钉螺存在的水域都是疫水,现在差不多整个洞庭湖都是浓稠的疫水了。洞庭湖区,由于不可能完全摆脱疫水环境,血吸虫病的重复感染率可以高达47%以上,所以,染病的也不一定非下水不可,疫水溅到你身上或是滴到你身上,尾蚴就闪电般上身,那时间只要10秒,湿地草丛间的露水也是疫水,鼠、狗、兔、羊、牛、猪以及狐狸、黄鼠狼、獾子都喜欢在草丛间磨蹭,哪有不得病的道理。
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一个重要链节就是粪便管理,我们现在连人粪管理都十分困难,哪里还管得上兽类的遗矢?于是兽类的遗矢也大量污染水源,一头病牛的一次病原传播可以抵得上100个病人,八百里洞庭湖四周有无数的野物出没,你管谁去……
至于外乡渔民,流动性强,没有户籍,只要你想想我们现有的百万病人大军,你就知道我们实在无力顾及他们了。
9月26日,我们渡过长江,重返14年前到过的荆州地区,寻访当年的采访对象,全国劳动模范,血防专家胡国富。
民谣说,全国疫区数湖北,湖北疫区数荆州,荆州疫区数岑河。岑河是一个大镇,历史上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重疫区,国家血防攻关项目始终在这里进行,联合国血防专家戴维斯也一直在此蹲点,胡国富当年就是岑河血防站站长,血防战线一干就是40年。
彼此见面的第一句话几乎是异口同声:血吸虫为什么越灭越多?
胡国富的回答令人大吃一惊:大家都讳莫如深的原因就是──基层血防“队伍打散了”。
至少湘鄂赣三省的基层血防专业人员多年来没领过一份象样的工资了,比如我,党员干部,献身血防40年,全国劳模,退休了,没有一分钱退休金,你不信?我这里还有一个全国劳模汶守德,和我一样一直是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你当年也采访过,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一分钱退休工资,如今摆一个烟纸摊过活。
什么“越灭越多”?根本就没人去灭它了,还不越活越滋润。
在国人的心目中,恐怖的血吸虫病早已成为历史,所以近来报道血吸虫肆虐状况时,往往使用了“卷土重来”、“瘟神再现”一类的措辞,这实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血吸虫病从来就没被消灭过,所以也谈不上卷土重来,而造成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当年写的两首《送瘟神》诗。你有没有注意到,毛泽东为之“夜不能寐”并且遥望南窗,欣然命笔的其实是江西余江县,那地方当时确实消灭了血吸虫病,但那只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面”。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我们只顾万口传诵,不求甚解,给人们造成全国都已消灭血吸虫病的错觉。
客观地说,解放以来,血吸虫病的确有过几次被遏制的时期,那就是大跃进时期、70年代中期、80年代末期。但“遏制”和“消灭”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血防史上,历来有“灭螺派”和“救人派”之分,前者“治本”,后者“治标”,治本当然令人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毛泽东就是治本派,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伟人气派。
问题是,钉螺是一种生物,一种“很腐败”的贝类,非常热衷干那事,一对钉螺一年半以后居然可以繁衍出25万只后代,这么一来,就像你要消灭蚂蚁、消灭蚯蚓一样,几百万亩甚至全国几亿亩的河湖港汊、洲滩沼泽、荒圩湿地,哪有彻底消灭它们的可能?
治标的“救人派”,主张把有限的财力用来救病人,保存农村生产力,把血吸虫遏制到一定范围内即可,但这几年血防形势突变,社会转型期,血防干部自己都活不了啦,还不先救自己吗。照此下去,“千村薜荔人遗矢”的悲剧没有理由不重现,“40年了”,他说,“我们这些专门‘送瘟神的’,没把瘟神送走,自己倒被 ‘送走’了”。
我说的是大实话。你们搞调查的,应该自己下乡走走,以事实来服人。
胡国富的妻子倪文英原是血防站护士,和胡国富一样在血防站工作了40年,退休了同样分文工资没有,幸亏当年在职时买了保险,否则老两口吃一口饭都成问题了。
“光荣的血丐”现在必须自谋生路
湖北有两件天大的事,水利和血防。每届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得过问这两件事。
“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血防成就还是很大的”,下乡前,荆州市沙市区血防办张顺金主任对我说,如果没有这样大规模的遏制,我敢说血吸虫可以把我们这些地区都给吞了,问题是,血防属于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关键一环,国家应该有可观的投入,湖北的血防形势一向是,国家大投入,螺情大遏制;国家少投入,螺情大反弹。道理很简单,如今没有人会从事毫无报酬的工作,只除了岑河镇血防站也许是个例外。
张主任属于区县一级的血防办,地方财政还拨给工资,每月800元,区县以下的就都没有了,可是工作都要下面做的,他说,我们现在都“不好意思”下去,就是下去也难以调动下面从事无报酬的工作。
岑河在荆州市的东郊,现有的血防站建筑还是当年胡国富任站长时发动职工集资盖的,那是血防史上最好的年头。
远远望去,当年的全国劳模汶守德正表情木讷地练著摊,摊前苍蝇飞舞,污水横流,同行的告诉我,他每天的营业额不满15元,我不忍心去招呼他,便径直走进了血防站。
这也许是荆州地区极少数还苦苦死守著的血防站了,现有职工32名(含9名退休职工、1名癌症病休职工),原来的工资标准,站长以下到职工,800元到500元不等,自1996开始只拿15%的工资,2002年开始,就分文没有了。
高温天气,“血防红旗单位”内没有一台空调。没有X光机,没有台式B超,没有手术床,二楼病房内倒有几个病人躺著,“晚血”。肚子大得像坟包,肚脐爆得像菜头。
他们居然还到你们这样的地方看病?我问副站长杨继新。
他们也只能到我们这样的地方来看病,站长李顺湘接口说,穷啊。我们收费标准低啊。全镇总人口46000多人,血吸虫病人倒有4000多人,如果吃中药,那就几乎家家户户有药罐。
国家以前收治血吸虫病人不都是免费的吗?我说。
早就收费了,都10多年了,李站长说,前些年,“晚血”病人还可免费,现在“晚血”病人也收费了,当然,对特困的晚血病人,政策上还有补贴,但那是撒胡椒面,“大头”还得自己出。
他为我算了一笔细账,一个慢性血吸虫病人一年的最低治疗费用是200元(不含生活费、营养费),一个晚血病人一年的最低费用是5000元(不含生活费、营养费)。
2002年,岑河镇的慢性血吸虫病人为治疗总计花了79.6万元;晚血病人为治疗总计花了32.5万元�@习傩找荒昃褪?00多万的支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所谓“因病致贫”,一个富裕之家(我们这里的标准是3万元即可称富)只要有一个“晚血”,就完了。
千万别以为这些治疗费都进了我们的口袋,我们这里只有最穷的甚至没有支付能力的农民才光顾,有点办法的都去了省市医院,所以我们现在为谋生计,什么病都收治,老烂脚,癞疥疮都收,这样的“创收”,每人每月还能平摊到300元(退休员工不计),仅够“不死”。人们称我们为“光荣的血丐”。
事实上,我们血防站的人员都感染了血吸虫病,真成了血丐,李站长说,“上面有人说过,疫区的干部,不感染血吸虫,就不是好干部!”
这样的队伍,没解散已经是奇迹,陪同的沙市区血防办副主任赵昌炎说,有没有可能和血吸虫作战,你们自己看。
按原先的建制,你们下面还有“灭螺队”,现在怎么了?
全部溃散了。按原来政策,灭螺队员从农民中遴选,不脱产,每个村民小组负担一名,每年付给他报酬1500元左右,每村有5-8个灭螺队员,这模式全国都一样。职责:查螺灭螺、防护宣传、疫情监测、是最前线最骨干的血防力量,后来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全撤了。没有了他们,我们就丧失了基本力量,20余人要在 15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查螺灭螺本身是个神话,更何况我们现在首先要糊口,所以,全部放弃了。
“全部放弃”的意思,是不是在广大的农村,“血防”已经不设防了?
是的。湘鄂赣的村一级单位,你给我去找一个像样的灭螺队来。
国家每年不是还给你们下拨3吨灭螺药吗?
3吨药只够灭螺40亩,而岑河的钉螺面积近7000亩,撒味精“味屁”都没有。我们只能把药撒在镇周围,不让它们攻进来。
那……为什么还不解散?
第一,解散了,连现在的“创收平台”也没有了,老话说还没有“见尸”;第二,等著有朝一日,兴许国家又会想到我们了,再次起用我们。第三,兴许有社会力量关注血防,发起一个善举,捐一架彩色B超给我们。这第四嘛……我们至今还不愿意相信,血防真完了?任凭这里浓稠的疫水烂到下游,烂到江苏、上海去?
早就有人劝我们去北京上海要饭,说那里要饭的也有千儿八百,这是侮辱我们,搞血防的,不成功便成仁!楚虽三户,灭秦必楚。
这只是“光荣的血丐”,等待反攻,悲壮而已。胡国富说,岑河镇刚解放时除了“阳湖岗”一地外,基本没有钉螺,属于湖沼地形,后来大兴水利,变成了水网地带,“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遂成燎原之势,一遇排灌季节,疫水就通沟连渠,串塘过田,搞得阳性钉螺“螺天螺地”,人们越病越穷,越穷越病,“晚血” 的,家家家徒四壁。
我们考察了“晚血”病人张克勤、范后香的家,前者消化道大出血,后者高度腹水。
张家果然只有墙了,全家四口,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床是没有的,稻草铺地,盖的是烂棉絮,不似渔网胜渔网,肝腹水肝硬化是用药的无底洞,所有可以变钱的都变钱了。
范家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奄奄待毙的病人,家里几乎没有活物,没有一只家禽家畜。“为什么不养一只鸡鸭?”我问,可以拣一些蛋,补充营养。
人食都没了。哪有鸡食。丈夫童元柱回答。他也是血吸虫病患者。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同行的说,这样的场景不知何故会令人想起三国袁术败亡时断粮乞食的对话──袁:“可有蜜水?”答:止有血水,安有蜜水?
一旁的赵昌炎副主任说,还是看看一个已经“见尸”了的血防站吧。那里的血防战士也在“硬拖”著。
那叫观音垱。也是一个镇。疫区人口5万。
观音垱血防站彻底解体了。支部书记兼站长王玉华已经完全不上班,是被赵昌炎临时叫来的,“谁知道他在家里鬼混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活的”。
王玉华圆鼓鼓的手慢吞吞地打开锈锁,推上闸刀,接通电源,为自己辩护似地嗫嚅著:我们全散了,湖南湖北乡镇一级的(血防)基本瘫痪了,又不是我一家散了,我怕啥。
3000平方米的血防站楼高3层,1992年竣工,大堂里的一幅壁画《黄果树瀑布》还能依稀显示当年开业时的盛况。
所有的房间都空空荡荡,走廊里,到处是烂纱布,破药瓶,旧病案,秋风不识字,乱翻病历卡,一派大溃退的景象。
“我有什么办法”,王玉华胖嘟嘟的脸上挤满了无奈,指指一排排的空房,“老百姓的家还没有来得及‘鬼唱歌’,我这里已经夜夜‘鬼唱歌’了。”
没有一分工资,大家要走,我拽也拽不住。什么坚守岗位?你不给人薪水,说话就没有底气。原有编制16人,现在只剩我和统计员两人算是留守,今年1月到9 月,我们俩总共只拿了360元,“我想把它给卖了”,王玉华指指屋顶,满不在乎的模样像是一个农民要卖他的牲口,“用了10年了,还有五成色吧,卖它个 30来万再说,还债。”
关了一年了。上面每年给我一吨药,我就撒撒附近的水面吧,他补充说,副站长张如福自己开门诊了;一个护士到广西打工去了;一名女医生改行,到药厂去搞包装了;另有一医一护去了318国道边开血防门诊……就剩我了,转业军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任何收入,现在靠老婆养活,再看它一年,还这样厚颜无耻靠人养,明年就走人了,我不能老吃软饭。
观音垱的疫情怎么样。我问。
还能怎么样,一对钉螺一年半以后就是25万只,观音垱原来就有无数的钉螺,现在怕是要计划生育了。
“卫生部实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以来,你们怎么执行?”
填数字呀。数字出干部啊。灭螺队全部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习惯“估报”、虚报了。这,还不是公开秘密?走,有机会还是看看螺去吧。
天下最令人头皮发麻的事大概就是查看钉螺了:河滩上,芦苇边,扒开一块草皮或者轻掀一片湿漉漉的瓦片,下面立刻是鱼鳞一样排列,麦粒一般大小的钉螺方阵,黄褐色,蠕动著。要是富于联想,你应该想到血汪汪,血汪汪。
忽然想起岑河血防站的介绍,他们都是在查螺时感染的,不由糁得腿肚子阵阵转筋。
余江没有螺情,血防之路何在
我们把“余江红旗”放在最后,并不是刻意要为文章增加亮色,而是它的确是一道亮色,一个例证。
江西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共有37个县(市、区)3274个行政村流行此疫,尤以波阳湖沿岸8县为甚,截至8月底,全国实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以来的一个月,确诊江西“急感病人”90名,“急感”疫情主要集中在波阳、余干两县,占全省报告病例数的四分之三。
但是余江县却依然安如磐石。
1958年5月,余江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在全国率先实现以县为单位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创举,在血防线上树起第一面红旗,毛泽东为此写下了著名诗篇《送瘟神》,余江至今已连续巩固血防成果45年。
从南昌到余江县3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路程,县血防办主任郑录春说好了在新落成的“送瘟神纪念馆”前的广场等我。
国家投入不投入到底不一样,新落成的“纪念馆”高耸而堂皇,三个大展厅,大会堂一样高敞。郑主任说,它始建于80年代,当时国家拨款40余万,这次重修,又拨了200万。
我们的血防办就在楼内,他说,大概是世界上条件最好的血防办了,在职职工16人,人均月工资900元,所有的退休员工都有养老金保障,上面说了,再饿不能饿孩子,再穷不能穷血防,因此我们的“人头费”和办公经费每年都确保30余万,再加上省“血地办”每年下拨的5万元专项经费,大家的确干劲十足,没有后顾之忧,稳定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血防队伍,以至于1958年6月30日在《人民日报》报道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新华社记者刘光辉,时隔40年再访余江,走遍了余江大地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血防战线的“第一面红旗”的确没倒。
和无数的记者类似,我也带著怀疑的眼光来到余江,来到著名的兰田畈,一心想挖个钉螺回去。
如果说,当年余江县是全国首先消灭血吸虫红旗,那么,兰田畈就是余江县最先消灭血吸虫的先锋。
下午的兰田畈非常安谧,一看就没有“钉螺村”所固有的那股子“戾气”,村民在水边活动,就像人们在海滨浴场徜徉。
记者见多了,村民对生人的态度非常和蔼自然,71岁的姜炎万老汉,曾经是“晚血”病人,巨脾切除,他说:“1958年前我们村民都有血吸虫病,当时我才26岁,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毛主席派医疗队来到我们村,免费为我打针、送药,我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
血吸虫是怎样灭的?我问。
当年,工作组带领全村开展轰轰烈烈的灭钉螺运动,有药物灭螺,五录酚钠,也有工程灭螺,填旧渠,挖新渠,除草灭螺,大家去河边、田里捡钉螺,捡得越多越上表扬,苦干了几年才把钉螺全灭了。
那现在呢?
现在彻底没有了,上面每年都要来查钉螺,查得可紧了,像查通缉犯一样。
“血防在湖北是天大的事,螺情在余江是天塌的事!”郑录春接著姜老汉的话说,1973年“好不容易”在白塔河查到一只,县委立刻连夜召开常委会分析研究,发动干部、群众3万多人,堤上堤下趴著,沿河“爬梳”查螺39公里,直到查清螺情才罢休。这里是绝对不允许有螺的。
信不信由你,我们这里有的乡镇全年都悬赏收螺,每只钉螺悬赏30元。作假不但倍罚而且从此不为人们所容,因为你亵渎了余江最神圣的事。
余江的奇迹令专家欣喜,也令专家忧虑。
因为奇迹总是个案,而个案并不一定具备普遍推广的可能性。
全国血吸虫病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兴建教授认为,余江的奇迹正好说明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强化,必须要有政府的投入,今年春夏 “非典流行”,中央财政一个月内四次下达对地方的非典防治专项补助经费,累计补助资金总额4.4亿元,立刻就控制了局面。
而血防呢,从其机构的设置变迁,就可以看出它地位的微妙变化,“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成立于1955年,至1986年撤消,这个时期是中国血吸虫病控制最稳定的时期。
从这以后,国家对血防有所放松,疫情也就逐年反弹。
“领导小组”撤消后,“血防这一摊”就归入国家卫生部“地病局”、再降而归入疾控司寄生虫处……中央的财政投入也就逐年减少,90年代开始,每年对全国血防的拨款也就2000万元。绝大多数的血防资金必须由疫区所在省份自筹。缺�谑嵌嗌倌兀壳乙院笔∥?湘鄂赣三省中血防投入最大的)。
湖北省副省长刘友帆在2003年9月29日全省水利血防工作会议上透露:全省每年血防需要投入8000万元至1亿元,但实际只自筹了2500万元左右。
缺口也实在太大了。但于湖北而言,“已经好累”了。
湖北另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公共卫生专家说,血防目前的窘境,实际上还凸现了“市场失效”的危机。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过于相信市场经济的“活力”,过于相信它的杠杆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血防是一项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业,说白了就是“烧钱的公益”,而且还不是办报的“烧钱”、网站的“烧钱”,期望“烧钱”之后很快会有收益,对血防投入的收益将是间接的,长线的,将以广大农村逐步恢复生产力、广大疫区恢复社会稳定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发展作为深厚回报,政府根本不能期望目前的血防体制能够“自己造血”、先养活自己,再“兼顾性”地遏止血吸虫病的蔓延,也不能期望农民自己来买药杀螺,血防的确有自己体系的医疗机构,如各地的血防医院、血防站,然而一旦把他们推向市场,就等于把血防推向了不作为、推向了“不设防”,目前基层血防的不作为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一些专家认为,余江对全国的贡献、对血防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但同时,他们得到的 “倾斜”也是明显的,国家重视、省里重视、县里更重视,“再穷不能穷血防”。我们一些地方显然就做不到这点,“再穷就是穷血防”。血防没产出、没效益、没政绩,搞好了是应该的,搞砸了就是“砍旗”,年轻干部避之不及。
再从灭螺条件看,余江也具有不容否认的地理环境优势。
中国消灭血吸虫之难,难在各种因素互为恶果。首先长江、洞庭湖、鄱阳湖就是血吸虫最大的“孵房”,广袤浩瀚的沙洲圩滩芦苇荡里日夜孳生著恒河沙数般的钉螺、尾蚴,在现有条件下想根除它们,“门都没有”,而且几乎永远没有这个可能性。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谈所有农田内的灭螺,我们姑且假定长江两岸、洞庭湖沿岸、鄱阳湖沿岸的千万亩良田都已经彻底消灭了血吸虫。但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旱之年你开不开闸?只要开闸引水,进来的就是长江、就是洞庭湖、鄱阳湖那浩浩荡荡的疫水。
更何况还有长江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洪涝灾害。湘鄂赣三省血防45年来周而复始的噩梦就是:无数已经除灭了钉螺的“红旗田”、“红旗圩”,只要长江和“二湖”一咆哮,一场“通沟连渠,串塘过田”的“大疫水”就把人们多年修成的正果毁得干干净净。
因此,“彻底灭螺”近年来为学界不取,也许只有胡国富的含著眼泪的玩笑才能灭螺:哪一天钉螺被证实是天然的“伟哥”,钉螺的末日才到了。
故而智者止于“遏螺”。
余江的自然条件又不一样了,地处鄱阳湖上游,而且是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没有太多的河湖港汊,不受鄱阳湖疫水倒灌的影响,唯一的水源就是水量充沛的白塔河,而且是先经余江,再赴鄱阳湖,只要全体人民努力,“毕其功于一役”不但可能,而且已经巩固了45年。
所以,“奇迹”至今还是一个光辉的个案。
正如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与预防司一位官员日前对记者所言:“血防工作从总体上看,不容乐观,它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那么,人虫情仇何时了。
突破口已经有了,那就是我们的攻略思路完全转向,由螺本体转向人本体,通过疫苗研制完胜血吸虫。
但是,在血吸虫疫苗正式用于人体之前,我们的血防将注定像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西绪福斯”所从事的悲剧性劳作,将神给予的巨石推至山顶,坠而复始,乃至无穷……
转自新世纪(首发新民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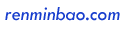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