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西晋的大文学家潘岳,写过一篇很高雅的《闲居赋》,但实际上,却是个谄媚的小人,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难怪元好问要写诗讽刺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元好问自己呢,却又因事涉为叛将崔立立碑颂德问题,大节颇有争议。
但我们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
鲁迅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小百姓们早就不满意于文人的此种所为,所以对那些落拓不羁者情有独钟。戏曲《太白醉写》中突出地渲染李白要杨贵妃捧砚,要高力士脱靴,大概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但到了近代,情况有些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的生活来源较前有所不同。他们不必再靠王公贵族的供养,而可以通过卖稿、卖画或剧场演出,从读者和观众中获取生活经费。鲁迅在论及梅兰芳时,说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这就道出了演员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如果文人的习性不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照样会出现新的帮忙和帮闲。他们可以从依附皇室豪门改为依附富商巨贾。明清时代,扬州盐商门下的清客,就是帮闲的新品种,他们照样为主人做着消闲解闷的事,无非是改换一下门庭而已。倘以此种习性来对待读者大众,用鲁迅的话说,也可以变成大众的帮闲。
中国文人,古代称之谓“士”,现代则称“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不仅是称谓的变化,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指出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二是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工人阶级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的性质的差别,即前者是从事脑力劳动,后者是从事体力劳动,而其形成条件则是相同的。
我国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为己任,敢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无论是写小说或者是写杂文,都着重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对社会一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他的硬骨头精神来的。
鲁迅一向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他还说:“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坟·摩罗诗力说》)鲁迅是生活中的强者,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生活中的强者不是以多制寡、党同伐异的人。鲁迅反对跟在众人后面鼓噪,蹲在影子里面摇舌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因为这些人的心理是很卑劣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生活中的强者也不是以强凌弱,在嫩草地上驰骋的人。鲁迅说,在大道上,不能只看到羊和凶兽两样东西,其实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种变性变态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是很可悲的。“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了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国家是好不起来的。所以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鲁迅的思想充满辩证法。这是强者的辩证法,而不是卑却者的“辩证法” 。
毛泽东称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认为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两句诗,也正是这种强者辩证法的体现。
对于孺子,鲁迅是爱护备至,充满牺牲的精神。他在《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里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决不是空言者,他为青年做的许多事,就是明证。
对于强暴者,对于压迫者,他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仗义执言,和名流学者评理,和权力者对抗,在被无理免职之后,他又敢于控告顶头上司,终于取胜。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预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即使自己被通缉,最后只好走出北京,也决不后悔。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前,他敢于揭露残杀真相,悼念被害战友,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
中国人由于状元瘾太重,什么都喜欢追求第一,追求卓越,追求辉煌,而不愿做平凡者,更耻笑落后者,蔑视失败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样的国民,在平时则附炎趋势,若遇到敌人,必然是“土崩瓦解”。有鉴于此,所以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鼓吹“不耻最后”的思想。他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见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追求平凡的韧性的战斗者。他在《过客》里,塑造了一个蓬面垢首,衣衫褴缕,不受布施,而永远向前行进的老人的形象;在《这样的战士》中,塑造了一个不受敌人迷惑,能够掷中敌人心脏的高举投枪的战士。他们都体现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风骨。
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高扬鲁迅风骨!(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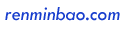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