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追踪报道,增城市康宁医院是广州外来盲流病人的定点收治医院。该医院实际上具有治疗和管理两项职能,但这家医院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收治区管理极其混乱。康宁医院的管理混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江苏女青年被轮奸。
对此,该医院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收治区负责人、精神病科副主任黄义福负有直接责任;院长郭镜航对医院混乱的管理情况熟视无睹,负有领导责任。目前,黄、郭已被立案侦查。
广州市卫生局已于日前撤消康宁医院为外来盲流病人定点收治医院的资格,另行指定收治医院。
相关报道: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
一位湖南少妇,刚出广州火车站,就被人抢走行李。接着,警察来了,可警察不但没有帮她找回行李,反而认定她是精神病患者,并把她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在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她被众多暴徒轮奸了……
涂同、苏萍夫妇是湖南人,去年7月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随后,丈夫涂同到珠海,妻子苏萍则回江苏娘家筹款。然而,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毁灭了这宗生意给小家庭带来的美好憧憬。
警察把我送进“地狱”
今年7月16日,也就是那场飞来横祸发生一年之后,在几位热心的记者资助之下,已患有严重精神恐惧症的苏萍,由其父亲陪同专程从江苏赶来广州,在本报广东记者站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一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那天(1999年7月11日)中午,我下了火车,一手提着一个皮箱,肩背行李包,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
当时天正下着雨,广场乱哄哄的。突然,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几下就抢走了我的皮箱和行李。
我惊呆了,继而坐在地上大声哭喊。箱里不但有我的全部衣物和家用,而且还有向亲朋借来的4000多元钱。我今后怎么过啊!庆幸的是,胸前的布娃娃没有被抢走,因为怕出意外,我特意将8000多元缝在里面,时刻紧紧地抱着。
这时候,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警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的一间临时留置室里。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话也不问,又强行把我拖上了那辆警车。我死活不肯上车,并大声申辩,但他们毫不理睬。最后连我想捡起放在留置室椅子上的布娃娃,也不允许。
大约黄昏时刻,车到了康宁医院。我被强行拽了下来,投进该医院二楼的一间房里。
里面有几个老太太,也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他们围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着。
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我。我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但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
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我?我也说不清。当时他们强奸完我后,可能是看到我已经昏死过去,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梦半醒中,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只是觉得又饿又累,同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也在被人强奸。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
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
当地公安局把啥都否了
1999年7月12日晚上10时多,在珠海打工的涂同接到湖南邵阳老家打来的电话,称增城市康宁医院电话通知,苏萍因精神病被关在该院,需要一笔钱治疗。
涂同满脸困惑,妻子临走时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成了精神病?他叫上一个同事,连夜赶到增城市,几经周折,于次日凌晨2时许才找到康宁医院。
“她见到我们就大叫,我第一眼看上去,她已经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上衣扣子也没有扣好,裤子很脏。”涂同痛心地说。
两人把苏萍叫到门外边。苏萍流着眼泪小声地告诉丈夫,她被屋里的人轮奸了,她可以认出那些人。饱受惊吓的苏萍一再提醒丈夫,这里的人很凶,千万不要大声说话,也不要吃这里的东西,吃了以后会晕倒……
涂同要将苏萍带走时,一个被称为“牢头”的男子说:“这要等老大来。”一直挨到早上8时多,收治区区长黄义福来了。涂同向他交涉,要求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黄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从开初的2000元降为500元。涂同交完款,取了收据,这才领走苏萍。
一出了医院大门口,苏萍号啕大哭。同样感到悲痛欲绝的涂同赶紧向110报警。大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骑着摩托车的民警,将他们3人带到当地的增城市镇龙镇公安分局。
涂同说:“办案的警察很不耐烦,简单地问了几句,当时没作笔录。”后来,他们派了四五个人,与涂、苏等人一起来到康宁医院。
镇龙镇公安分局就在康宁医院的旁边。在精神病盲流收治区内,民警命令里边的所有人站成一排,让苏萍指认强奸她的人。苏萍当场指认出八九个犯罪嫌疑人,并说有很多人围着看,那个看门的人强奸了她两次。
指认后,涂同提出,房间里的席子上有明显的污物,要求警方将其作为重要的物证带走,并控制被指认的犯罪嫌疑人,防止他们逃走。但是,民警没有理会。
民警刚走不远,苏萍夫妇突然发现,有两个被指认的犯罪嫌疑人被放出来了。涂同立即追上去向民警报告,这几位民警只好将那两个被放出来的人和“牢头”扣起来,并责令医院不要放人。
下午,民警叫来法医,将苏萍带到康宁医院做检查。尽管涂、苏二人坚决反对到案发医院检查,但没人理会他们的意见。等他们一行再次来到康宁医院时,涂同吃惊地发现,原来污秽不堪的席子、地板已被擦洗得干干净净,不懂办案程序的涂同本能地意识到,案发现场最重要的证据已经被人为地破坏了!
做完鉴定已是下午5时多,涂同又买来一条新裤子,给妻子换上,将案发时那条上面沾有暴徒们点点精斑的裤子作为证据留给警方。
之后,涂同从查阅到的被收容人员登记表上看到,妻子是被广州市流花公安分局以“精神病患者”的身份送到康宁医院的。表格上填写的内容是:姓名:无名氏;性别:女;年龄:35岁(实际年龄为26岁———记者注);收容原因:有精神病。下面有经办人、流花公安分局巡警刘国宏“建议收容治疗”的签名,批准人为苏左友,日期为7月11日。
回到珠海后,涂同还是不放心,他于1999年7月27日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该院很重视,随即将控告材料转往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同时告知涂同,案情重大,应立即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举报。涂同夫妇为此深受鼓舞。
但就在这时,针对涂同夫妇的举报,增城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说,经过调查,“没有这回事”。夫妻二人悲愤交加,当即赶往广州,先后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举报和反映情况。
应当说,上述几家单位对此事是重视的,其中,广东省公安厅当即指派广州市公安局有关领导接访。该局当即兵分两路———到流花分局调查情况并查找布娃娃的下落,后涂、苏二人得到的消息是“布娃娃被当作垃圾已扔掉了”;而另一路人马带着涂、苏到达康宁医院调查。
此时距案发时间已20来天,涂同说:“在医院,当时被指认的那些人都被放跑了,又来了很多刚被收容的人。”
而且,时至今日,虽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检察院都受理了涂同夫妇的控诉,但经涂同的无数次催促,以上单位至今没有给这对夫妻出具任何对事件的调查报告。
是医院还是毒瘤
今年7月11日和12日,记者两次来到位于广(州)汕(头)公路旁的康宁医院。该院院长郭镜航对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回答,只是反复强调要经过上级批准。
此后,记者来到增城市卫生局。据该局局长陈德棠介绍说,康宁医院是增城市卫生局下属的一家综合医院。在1988年广州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的文件和1993年广州市卫生局文件里都规定:收治广州街头的病卧、伤残及精神病“盲流”,通常由收容遣送中心收容后送到康宁医院,经过治疗后再由收容遣送中心负责遣送至原籍。
康宁医院副院长高水容说:“按照当时的计划,收治这部分‘盲流’的床位是足够的,但后来人越来越多,床位变得越来越紧张,因为是公安、民政和卫生部门3家共同管理,经费问题很难协调,所以,收治精神病‘盲流’的条件很差。苏萍被作为‘盲流’收治后,放在一个大区,晚上没人值班,也没有保安,存在很大的漏洞。”
据调查,当晚收容苏萍的精神病“盲流”收治区,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负责收治和管理精神病“盲流”的康宁医院精神病科副主任黄义福向记者说,苏萍不是广州市里的收容遣送中心转过来的,是由流花公安分局的两位民警和一个“马仔”送来的。她当时不肯下车,是强行拉进去的。“我在收容单上签了名,然后由我们这里比较清楚的人带进去的。”黄义福所说的“比较清楚的人”,是指被收容的无精神病的“盲流”。
但黄义福表示,他在查房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强奸案。“在12日下午,我又去查房,她写了个电话号码和自己的名字,我问她是不是叫苏萍,她点头,又问她电话号码对不对,她肯定地点了点头。我一看区号,是湖南邵阳的,离我的老家郴州很近,就产生了同情心,在当天晚上给她家打通了电话。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她老公来把她领走了。直到公安局的人来了,我才听说里边发生了强奸案。”
黄义福记得,当时房间里被收治人员有30多个男的,以伤残的为主。“公安局的人来到后,叫她认人,我也进去了,她当场认出了10来个。”
康宁医院副院长高水容翻开笔记本说:“7月16日公安局带走两个,17日带走34个,还有15人没有带走。这些人都是那个收治区的,有一部分是后来被收容进来的,反正公安局把他们带走后,也没有办任何手续,我们至今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轮奸怎么变成了强奸
1999年11月初,苏萍收到增城市人民检察院于10月19日签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通知书》,称该院将对在康宁医院涉嫌强奸犯罪的被告人李文明(湖南省怀化市人,25岁)提起公诉,告知其可以委托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与此同时,广州市公安局信访处与流花公安分局一行6人专程前往珠海,当着涂、苏的面表示,对此事的发生感到痛心,将对有关直接责任人予以除名处理,同时送上2000元“抚慰金”。
1999年11月18日,苏萍委托律师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对增城市康宁医院、广州市流花公安分局和李文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上述3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20104.8元,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今年1月6日,增城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将广州市公安局流花分局及增城市康宁医院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诉讼主体不成立,驳回了苏萍的起诉。
更令苏萍及其代理人感到不解的是,分明是增城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却将其称为“自诉”案件。后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对此予以纠正。
今年5月17日,增城市人民法院下达“(1999)增法刑初字第346号刑事判决书”,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李文明有期徒刑4年。审理过程中,法院也已查明“苏萍无精神病史”。
但是,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苏萍没有接到增城市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涂同说:“我们向法院递交了附带民事诉讼状,办理了委托手续,留有详细联系电话,但开庭时法院没有通知我们,非法剥夺了我们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而获得赔偿的权利。”
根据增城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这显然只是一起普通的强奸案。那么,案发时被苏萍指认的那些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增城市卫生局向记者提供的一份“通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市康宁医院收治区是广州市收治病卧街头‘盲流’病人,以及‘盲流’精神病人的定点单位。但该院收治区管理十分混乱,基本上无收治规章制度及管理,所收治的病人,男女病人长期混住一室,导致今年7月11日一女性收治人员被男性收治人员轮奸多次……”
记者试图从增城市公安局解开这个谜,但该局一位姓李的办公室负责人说:“我们是当事人,不好说。”记者问他,公安局为何成了当事人?他说:“当时接警的时候,镇龙镇公安分局在出警时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他避而不谈。
苏萍的委托代理人黎明律师向记者证实,他阅卷时发现,李文明供述,当时对苏萍实施强奸行为的有五六个人,他叫不出名字,只知道外号,比如“小四川”等。李还供述,连续两个晚上都发生了强奸行为,有一个被收治人员将苏萍带到三楼强奸,此人后来也被放走了。
案卷中还有一个被称为“牢头”的被收治人员的供述,他承认自己强奸了一个被收治的“东北妹”,而“东北妹”也曾被多人强奸,但因为“东北妹”没有告,也就没有人出来管这个“闲事”;同时,“牢头”亦亲眼目睹了苏萍被多人轮奸的过程。
黎律师还说,从卷宗中看,李文明、“牢头”等人的供述,与苏萍的指控基本是一致的,这表明当时发生在康宁医院的确实是一起性质恶劣的轮奸案。
那么,其他的涉案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逃脱的?这家医院到底还有多少事情被掩盖?至于增城市人民法院为什么在开庭时不通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庭等问题,记者欲要采访时,该法院以“记者采访要经过上级批准”为由,将记者拒之门外。
7月14日,获悉增城市人民法院作出对李文明的判决后,涂同匆忙赶到增城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抗诉申请书。
就在记者即将完成本稿的时候,涂同又给记者来电话。他说,有关机关已驳回了他妻子对增城市人民法院判决的抗诉。他绝望地问记者:“还有没有百姓说话的地方?”
(注:为保护受害人,文中苏萍、涂同均为化名)(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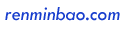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