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英第三次拿起又放下了《铁水奔流》。看不下去,列车也确实颠簸得厉害起来了。心绪真乱哪!……
真是料不到的事。她提前二十三天结束了这次采访。几个不痛快竟都发生在一天里。早晨两点钟,白班的矿工打着手电从二十里外翻过南山奔矿里来的时候,黄佳英违背着自己的意愿撕碎了最后一遍草稿。一整夜的工夫都白花了。下午三点钟,在矿长办公室里发生了一次争吵,争吵的结果是党委会会议对她关上了大门,不让她列席参加。三个钟头以后,就接到这封莫名其妙的电报——“速归”。她知道,这也不是甚么好兆头。
一般地说,凡是出来采访的记者,很少有心满意足、泰然自若地跨上归途的。不如意的采访使人惆怅,背上的行囊就仿佛无形中加重了分量。采访顺利的时候,五光十色的印象和思想又会在记者心里大吵大闹,要求出路。而对于一个有心的记者,归途又往往是一次新的采访的开始……。现在,当黄佳英无聊地数着车窗外蓝色大海里悄悄飘浮过去的灯火的时候,这几种心情同时都有。不过,扰乱她安宁的,主要还不是这些。
这七年采访、编辑生活里,无数消息、通讯从她手里流向了排字房。手忙脚乱地编写三百字的紧急消息,无限烦恼地从杂乱的材料中寻找串起它们的那条线,焦思苦想地琢磨几个字的标题,以及发走稿件以后焦急的等待,见报后为编辑部粗劣的删改而感到的懊恼……这一切,她都体验过不知有多少次了。
不,此刻占据着她的心的,也不是这些东西。作了三年记者,黄佳英还是不能习惯于怀着顾虑来写稿。而顾虑却偏偏要来找她。昨天夜里就是这样。主题早就想好了。跟往常一样,刚坐下来,最费力的是安排事实,组织材料,来最有力量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架子刚一搭好,她的思想就离开了笔记本和稿纸,朝编辑部飞去了。这样一篇稿子,工业组是不会作决定的,一定要拿到总编室。总编室主任马文元是这么一个人,在十篇别人拿不定主意的稿件里,也许有一篇他是肯作主的,其余就要转到总编辑跟前。总编辑陈立栋对别人的请示是永远也不厌烦的,时间可能拖得久一些,但看他是都要看的。最幸运的,是他拿起来亲自抹掉几段,使这篇稿子尽量跟过去发过的稿子近似些,使作者的思想跟已经发表的社论近似些。但是,也有第二种命运:这篇稿子可能被总编辑认为“有很大的片面性,暂时不发”。实际上,因为它是批评省工业厅的;批评上级,在总编辑看来是要特别特别慎重的。
黄佳英使劲晃了晃头,一束又浓又黑的头发打得她的脸有点儿疼。要是这时有人看她一眼,一定会说:好一个傲慢的姑娘啊!其实这是她在对自己生气呢。人做事,总是不能不实际的。黄佳英性子再硬,她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写的文章能不能上报。有很长一个时期,黄佳英写的东西接二连三地变成了“内部情况”,被打字、印发给几个单位,或者变成约社外的作者写稿的参考材料。后来她学乖了:宁肯把文章的锋芒弄得钝一些,也要争取文章上报。这总比分发到十几个机关“存档”要好啊。
可这是多么困难而痛苦的事!昨夜她熬了七个钟头。一面写,一面把自己设想成总编室主任、总编辑和工业厅长,用他们的眼光来怀疑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又到笔记本里搜索新的论据来跟他们辩驳,就这样自己跟自己辩论着,妥协着,然后又翻过案来,再争论,再妥协,而文章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会儿多一段一会儿少一段了……就这样苦苦折腾了一整夜,最后还是一起撕掉了。就好像她的心也被人撕掉了一样。
无论烦恼怎么多,一坐上火车,黄佳英的心绪就变了。坐火车,多么久她也不觉得厌烦。靠在车窗旁边朝外望去,每个村庄,正在建造的桥梁,都能引你想起许多事情;有时想得那么快活,有时又想得那么遥远。如果是夜里——像现在这样,那就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想吧,探求吧,生活是多么有趣!……对面坐着的那个小伙子,又睡着了。他睡得真甜哪。
棉袄从腿上溜了下来。黄佳英帮他盖好,一只手无意中又碰着了那本《铁水奔流》。黄佳英翻开它,却又立刻合上了。为甚么许多小说里把生活和人物都写得那么平常、那么清淡又那么简单呢,好像一解放,人们都失去了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一下子都变成客客气气、嘻嘻哈哈、按时开会和上下班的人了。有的书确实像一个工厂的大事记。也有人说过,这叫记录生活。难道生活原来的面目就是那样的么?
不,一点也不对!就说对面坐着的这个青年工人罢。他叫刘世福,是个钳工。从前年调到贾王矿的机修车间起,就变成了杂工;从今年二月起,又来了一批钳工,这儿连杂工的活儿也没有了。找人事科要工作,就说是“个人主义”;要求走,说这也是“个人主义”;给报纸写信,又说是,“无组织无纪律”,要他停职反省。刚才,刘世福想起这个人事科长来还忍不住笑:“我都闲得要报废了,他还说要停我的甚么职呢!”现在他跑了出来,要去给他们那儿八十名闲得难受的钳工找工作。路费也是大家凑的。可是坐上了火车,他还不知要到哪里去找工作呢。
想到这里,黄佳英心里有些感动,本来嘛,像这样的人是多么好,多么可爱!可是,她又有些替他发愁。他睡得多甜。可是明天怎么办呢,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报社每天都收到几封要求工作的人写来的信。这里需要钳工急如星火,那边呢?国家又得给无事可做的钳工每月支付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而人事工作者还得忙于“批判思想”……为甚么越是作人事工作的人,却常常最少考虑人的事情呢?……她猛然站起身来,躲着人们从座位上伸出来的腿,朝门外走去。从车门外吹进来一阵阵冷气,使人的头脑清爽多了。
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这三年里她看见、听见、懂得了多少事情啊!现在有多少事情使她常常受到感动啊!正因为使她受感动的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有些在她看来是缺点的事情,才使她那么激动不安。不像刚做记者的时候,有时兴奋得要叫,有时又无缘无故地着急。也许,就因为那感情的流变得更深了,因而表面上反而更沉静了?要是以前,她一定会把这个名叫刘世福的工人领到自己住的地方,把他安置下来,然后就放下一切事情,去替他和他那八十个朋友奔跑。现在,她想她不会这么做了。
她笑着想到,要是把这个工人领到总编辑陈立栋面前,他一定会说:“积压人才问题,我们发表过社论了!”当然,就是这社论,也是在党省委书记提示了以后,才去翻出了两年来存档的读者来信写成的。但是,发表得这么迟的社论在下面引起了多么热烈的反应啊!连从来不看报的这个刘世福都说他也看过这篇社论呢。而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多少生动的问题在报纸旁边流过去了。只有当党省委召开个甚么会议的时候,报纸上才把什么问题提出来。生活里那么多的问题,群众中间有那么多新鲜的思想和建议,党省委怎么能够来为它们每一个都召开会议呢?
黄佳英也知道,报纸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很不够的。报纸上的批评工作,也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虽然批评的都是县区以下的干部,但批评毕竟是开展起来了,而且出现了小品文这样比较锋利的批评形式——当然,美中不足的是,有的小品文写得过于轻松,反而不如一封读者来信有力量。最近报社里更是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空气:上上下下的人,都似乎更爱思考了,人们开始表现了争论问题的兴趣。连总编室主任马文元,也隔三岔五地表示表示他自己的见解了。到今年春天,情形有了更多的改变。党省委宣传部批评了报纸的单调和枯燥,一些编辑也提出:报纸应该怎么办?……就是这些情形,使黄佳英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有信心的。她就是有时候心里着急:再快一点儿罢!她也知道,有的事不能太急。可是一碰到具体事,她又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心思尽快地讲出来。就是不上报纸,找个领导同志谈谈也好。她害怕,当党的领导上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放松对另一个问题的注意呢?报纸是这样:总要等党省委把甚么问题列到中心工作里以后,它才拿大部分篇幅来报道那个问题……有几次,黄佳英想拿起笔来给党中央写封信,把自己在下面看见的某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和工人群众的要求告诉党,可是每一次都觉得材料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又想:也许中央早已了解了这些情况,正在研究呢……
她又想起来了:几个小时以前,她经过矿山的大楼时,礼堂里正在开矿上党代表会议。宽大的窗子里射出强烈的灯光,把地上的野草照得清清楚楚。依稀可以听见扩音器里的声响,大概是甚么人在作报告罢。黄佳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热辣辣的想法——她不知道这个会议上是不是会讨论到贾王矿那些每天只能睡四小时觉的工人,和刘世福这样长年无事干的人们的问题,她甚至想走进会场去,把召开那些无尽休的会议的人,和那个任意批判人而从不关心人的人事科长给说出来,把她听见的、自己想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提出来……
但是她又突然想到: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以后,她本来想找矿上的党委书记个别谈谈,可是又因为走得太急,没有来得及;一直到现在,她还在因为这一点而不安呢。到现在还不是个党员,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岁的女青年团员一切心事中最大的心事。
黄佳英从十七岁起就在一个机械厂里作职员。一年以后,家乡解放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介绍到报馆作检查员。在逐字逐句搜寻稿件里错误的同时,黄佳英还有多余的精力从别人的稿件中学习一些东西。有人嫌这工作刻板,黄佳英却爱上了它,作检查员每天看到的都是最新鲜的稿子;一个读者要几天以后才看得见,甚至永远看不见。黄佳英从那些写新人新事的通讯和消息里学习到的东西最多,因为这种稿件她常常看上几遍。以后,她决定作个记者。二十岁,一九五一年,她被调到工业组。两年以后,就去作记者了。
每一年鉴定表上都写着,黄佳英“工作热情积极”。但是,黄佳英一直到很晚了才发现自己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自己不去积极地找党,而总是等着党来找她,就这样把自己的入党问题拖下来了。
最近一个时期,每逢在外面采访,因为她不是共产党员而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极力使自己不要�咽堋!叭氲巢桓煤透鋈俗宰鹦挠幸坏愎叵担 薄3U庋搿?墒牵痪盼辶甑奈逶拢萍延⒙逯芩炅恕O衷谝残砘箍梢圆话炎约嚎闯梢桓觥俺渫旁薄保前肽辏荒暌院竽兀炕萍延⒒鼓芴感ψ匀舻夭渭油判∽榛崦矗俊旖ソチ亮恕3得磐猓汲鱿忠恢曛晔骱鸵蛔啬沟挠白樱幼牛频摹⒙痰暮屠兜难丈∠殖隼戳恕?p>那么快,不知不觉中,天空里出现了年轻而快活的一抹红色。清晨所特有的轻飘飘的凉意侵入了列车。黄佳英望着远远的天边,陷入到沉思里去了……十点钟,列车抵达尚武站。黄佳英想了想,还是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帮助这个工人!”她就赶忙走了过去,拉住刘世福的手,笑着说:“走,跟着我……”就和他一起往收票的地点走去。这时她一点也没想到,她究竟能为刘世福作些甚么。
她一面走一面忍不住笑,心里想的倒是:也好,总编辑要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说:“瞧,给你带来一封活的读者来信。无须调查,即可发表……”一想到快要到家,一个姿态优美的男人的影子就在她心里浮现出来。那人最近的一封来信还在她身上,居然还没有拆开。她不禁感到奇怪,怎么这些天来关于这个人她竟想得这样少,直到又要相逢的时候才忆起他来……
这又是一个烦人的问题。一阵忧闷涌上了她的心头。
转自大纪元
(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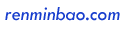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