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出自共產黨御用文人之手的文章也認爲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法西斯行爲,是對人施以嚴重的精神摧殘的手段,絕對是一種酷刑,會導致精神失常,並因此而對所謂的四人幫一夥人大張噠伐。我們同情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這些人。我們也對這種法西斯行爲深惡痛絕。
但同時也有一種怪怪的感覺,這東西好像似曾相識。再看了一遍細節,恍然大悟。原來94年到95年非法拘禁我一年半,是完全按照這個模式進行的。雖然我當時不把這當作一回事兒,可是這種模式就連看着我的小青年警察都有些受不了。24小時被盯着看的人固然非常難受,其實長時間這麼無恥的看着別人也非常難受。
在每天半小時放風的時間,沒有竊聽器監聽。我們習慣於悄悄地聊幾句天。我就問他們:盯着別人解手你就不覺得難受嗎?是不是有偷看女澡堂子的興奮感呀?小夥子的臉立刻就紅了,小聲罵道:王八蛋想出來的餿主意,孫子才喜歡看別人上廁所呢。就折騰我們這些小布拉豆子,那幫頭頭兒自己怎麼不來看別人上廁所。
我就教他說:下回你就站在廁所門外。頭兒要是問你就讓他自己到廁所裏邊來試試。他嘿嘿嘿地笑着沒說話。後來果然就站到了廁所外邊。我問他是不是按我教他的說了。他說沒有,他只是要求頭兒下次上廁所給他換換班。他對廁所的味道過敏。頭兒皺了皺眉頭也沒說話。這個負責看守我的頭兒是公安局的黨組書記。經常爲了安排這些超級法西斯的折磨人的做法,和防暴隊的小夥子們發生衝突。有一次竟然找我抱怨說小夥子們在食堂裏差點兒就揍了他。可見這種超級法西斯的做法,連執行的人都難以忍受。
可是他自己卻在我面前辯解說;這些連監獄都不允許的措施,是因爲沒有進入法律程式,所以可以不按照法律規定執行。「你要享受監獄的待遇,就要配合我們,快快地進入逮捕程式才行」。意思是說你沒罪也要認罪,否則就得忍受這種非法的酷刑。看來當領導就是比當執行者容易,只要夠無恥就行。
接着我就聯想到了,最近和艾未未一起被關進沒有進入法律程式的監獄的維權律師們。他們被關押的藉口和我當年一樣,監視居住。他們被折磨的狀況,只能比我當年更糟糕。所以被放出來的人連話都不敢說,大多數人都受不了那種折磨。甚至有人不得不讚美監獄的人道主義措施。這都是受盡折磨的後果。
可是聯合國和西方的那幫政客們在做什麼呢。他們只是問你:有沒有捱打,大多數人只好說沒有。嗯,好記錄在案。有沒有捱罵,沒有。嗯,好,記錄在案。還有人讚美中國監獄的人道主義措施。這就足以證明中國的人權狀況大大改善了。讚美者可以得獎,共產黨當然就不能去制裁了。殘暴的超級法西斯不是敵人,當然就可以和法西斯們進行全面的合作了。這和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們對待德國法西斯的態度一樣。
爲什麼會這樣?這就牽涉到了更大的問題,世界大戰能否避免,是不是會再來一次?西方模式的民主能不能克服金主政治的病根。共產黨和希特勒一樣聰明,早就學會了利用金主政治控制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按照共產黨的利益作出違反西方人民意志的決策。甚至不惜出賣西方人民的經濟利益,來滿足大企業和共產黨的共同需要。
用西方人民和中國人民的血汗錢養肥了超級法西斯之後。他們就不僅僅會危害人們的經濟利益,還會危害到人們的安全。包括作爲個人的資本家們的安全。這一次猶太人可能不會是唯一的受害者了。因爲共產黨和中國文化都不太看重種族主義,他們更重視的是階級關係。資本家們從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少好名聲的階級。他們能對付超級法西斯而保護自身的安全嗎?
但是資本家們會笑笑說:聳人聽聞,艾未未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中國窮棒子們的人權和美國人有什麼關係?二次大戰前他們也覺得自己住在法國、英國和美國,很安全。德國猶太人的人權和他們沒什麼關係。德國工會分子們和他們更沒什麼關係了。資本家永遠不懂政治,這也不是他們的職責範圍。危險的是他們卻能夠干預政治和輿論,把政治引向陷阱。
和年輕人們一起回顧這些歷史。會驚奇的發現;幸虧德國納粹沒有及時地製造出原子彈。否則這個世界現在是什麼樣子還不一定呢。但是展望一下將來,確實讓人不那麼樂觀。原來被文人們吹噓得上了天的戰後幾十年,這個世界並沒有接受過去的教訓。
納粹被禁止了,可是共產黨成了新的寵兒。還有無數納粹和共產黨變種的小專制體系。這個世界並沒有比過去變得更好。在金主政治的扶持下,人類被剝削和被壓迫仍然非常普遍存在。謊言仍然佔領着所有的媒體。酷刑和金錢都與時俱進地在發展着。艾未未們的遭遇不會比德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們更好。大作家茨威格描寫納粹酷刑的著作,看上去確實有點兒過時了。
那麼什麼是現實呢?埃及和利比亞人民的革命,也許是避免世界重新遭受戰爭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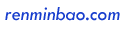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