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切嗜血、贪婪及残暴无度的专制制度一样,中共的这种制度是不需要由他人去颠覆的。这种制度下,权力机器的运动过程就是高产敌人的过程,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专制制度都不能长命的内在规律。专制的纯度越高,这个专制制度的寿命即会越短,这是颠灭不止的历史规律,“虎狼之秦”的短命足可镜鉴。人类制度运动史已彻底地证明,人类社会是可有长生不老制度的——产生于民意的,捍卫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权价值的制度。
几天前,当上海市近六十位上访者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望着他(她)们消失在严寒中的背影,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深痛,不觉中热泪涌流。脑海里,杜阳明老人无助的眼神,老人离开时深弯着腰用颤抖着的手去扣厚厚的外套时的镜头,想到他们在寒冷的冬日里仍随时面临的被抓捕的险恶,情久久无以自已。
近六十人的来访者,只有三、四个人未被非法劳教过,其余50多人无一人幸免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劳教暴虐!今天,我才有时间坐下来长时间地读看由他们亲笔签名的、饱含他们血和泪的控诉材料(材料中的字、词、标点均未改动)。
“我是董春华,今年已年近七旬。因不服行政违法和暴力拆迁,我的丈夫蔡新华(72岁)赴北京上访,被非法收容关押13天后遣送回上海,不料当天他即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2004年7月,我的小女儿蔡文君因赴北京上访,被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此后又因她去上海市信访办要求行政复议,又被冠以‘寻衅滋事 ’的罪名劳教一年,至今被关押在上海市青浦女子劳教所。”这位老伴因在上访时被非法关押十几日后突然死亡,接着上访的女儿也被非法劳教的老人写给我的材料上写着“一个老党员的控诉”。
“我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刘华琳,2004年2月22日我持车票乘车上北京,在上海市火车站站台上遭到上海市政府信访办206官员与另一同志的阻拦(至今车票在206官员手中),我朝出口处走准备回家,无业人员宋某和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洪某朝我冲来,那些不明身份的人围过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206官员目睹了这一切绑架、殴打行为,没有加以阻拦,我被打伤摔倒在地,他们数人将我拉起塞进一辆出租车内,被关进学校校长办公室一整夜,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参与。第二天又将我抬上面包车送到市公安局办公室,接受长达15——16小时的审讯,前后近30小时,不给吃饭、睡觉,不允许看病,丧失人性地进行摧残。在此期间没有出示过任何关押的法律手续。23日深夜,公安局姓谢的警察告诉我,公安局长要对我实施‘刑事拘留’,并扣上‘妨碍公务’的罪名。关进监狱,我被拘留20天后又被判以548天的劳教。在关押期间我的公职被开除,私人住宅遭强迁,财产被抢劫,包括钢琴、电脑及所有钱财。”
“在无端被关押五百多天的日子里,愤怒、屈辱、无助交织折磨着我,我教的学生无数,他们中有几个相信自己的老师是无罪而被政府关押的呢,高律师。”
刘新娟是这次来找我的上访者中被上海市政府迫害的最严重者之一。
“2003 年2月15日,我给‘市人代大会’送了三封信,16日上午8点,在去娘家的路上,发现有联防队员跟踪。一下车,我被编号41954的警察和七宝派出所、新龙村联防队拦住。41954警察用雨伞打我,至多处青肿伤痕,我被押上警车。在派出所没有留置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非法关押了两天两夜,期间41954嚣张的恐吓我,‘你已经告我们了,我们一定要把你搞透搞臭,要毁掉你终生,还要毁掉你儿子,房子不让你住,把你全国播放,你上访没有人相信你,我们只要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不肯给我验伤、疗伤,后来又押我到七宝医院,却不让吃医院开的药。18日,我被警察顾峰高、赵永林押到闽行看守所,这时才开出十五天行政拘留书。22日下午,看守所以治病为名,押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并对监狱人员说我装病。事实上,我当时已绝食四天,血压也很高,身体虚弱、全身疼痛。之后,我被关进戒毒者的牢房,全身上下被捆了五天五夜,每顿只吃两调羹食物,又不让喝水。我被他们像死人一样在地上拖来拖去。值班医生看我实在不行了,就给松了绑,开出B超检查。当时我已48小时没尿了。B超检查时,我恳求医生,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医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2月21日、27日,有关部门两次派人到看守所看过我,可以肯定,他们就是在这两次总共不到两小时的会面里偷偷给受尽折磨的我做了所谓的精神病鉴定。3月3号,也就是拘留十五天到期的日子,七宝派出所根据非法鉴定结论,不通知家属又把我从看守所强送到闽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关押,医院强制我服用精神病药。我每天站在医院病房的门口,通过探望其他病人的熟人才得以通知到家住附近的兄弟。在家属多方恳求下,于3月17日被医院关押了14天后才出院。由于在这段时间内服用精神病药物,精神受到摧残,暴力殴打致使后背脊椎骨错位,无法行走,只能以轮椅代步,继续信访,反映被非法迫害的情况。但迫害远没有结束,2003年6月3 日,我坐轮椅上访时,再次被七宝派出所强制送到闽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由于我不肯吃药,院方就强制我吃药、打针。对我的反抗,医院就动用多名医生、护士,男性精神病人对坐在轮椅上的我进行捆绑、殴打、撕坏衣裤,使用器械撬开嘴灌药,弄得口腔鲜血淋漓,注射针头把臀部肌肤扎得血流不止,喷溅到墙上。医生毫无人性,强制给我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注射癸氟奋乃静针剂。更为残忍的是,对每月只能用两针的药剂,医院却硬给我用四针。一位年轻的护士不忍心为我注射,护士长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边流泪边给我注射,因为她们深知药剂对没有精神病的人的毒害作用,第二针后我便痛苦地满地打滚。我责问医院陆科长:‘医院怎么可以没有医德’,陆科长直言不讳地叫嚣:‘这里不是医院,是监狱’。用药后的难受感觉真的无法忍受也无法形容,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昼夜睡不着,口苦得比吃了黄连还苦,眼神呆板、迟钝,眼睛睁不开,视力下降,连人的脸部都看不清,整个人精神崩溃,恍惚生命在慢慢离开身体。医院知道我的生命可能出现意外,前后又为我注射七、八针解毒剂。用药后的第五个月,我连数字都不会数,记忆力明显减退,完全是变了个人。医院的一位护工实在看不过去了,偷偷对我说:‘太残忍了,你这种情况,如果是北京来人调查,我肯定实话实说’。我曾在医院偷着借用他人手机给区长打电话,区长秘书表示知道我被关在精神病医院,但不肯救助。主任医生多次警告我以后不能再上访。我儿子多次要求医院、派出所放人,但他们互相推委,就是不放。我儿子又要求医院出示所谓精神病鉴定书,但对方以机密文件为由予以拒绝。我儿曾尝试担保出院、申请转院等方法,均遭拒绝。多方求助无门,我儿愤然割脉写下血书,寄往上海电视台。然而记者的到来也不能给予任何帮助,还关照我儿,我的遭遇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无法去申请鉴定,当地政府也不会允许我们轻易的去做这份明显对他们不利的鉴定。无奈之下,我儿和我父母、兄弟只能恳求医院、派出所放人,而派出所又逼我儿违心地多次写下保证书,保证我不再上访,并承担一切后果。受尽摧残的我终于在2004年1 月20日出院了,前后两次我总共被医院关押了246天。医院还硬要收取伙食费,否则不肯放人,为了救人只能付钱。他们给我母子缚上精神枷锁外加威胁压力,迫使我们无力也不敢再有反抗。任何人也无法再次承受长时间的残忍折磨。我儿因我的悲惨遭遇而受到牵连,又为我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却无力帮助,而在心理、精神上万分痛苦、自责。大学毕业后无心找工作。”
杜阳明老人的叙述:“2003年4月24日,我持函到闸北区信访办,被以莫须有‘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名处以刑事拘留一个月。2003年6月3日,在街道信访办被警察顾某某、翁某某、信访科长沉某某等人关押折磨近8个小时左右,将我双手反剪,屁股坐在椅子上,头掀到地上,身上留有多处伤痕(有照片)。最难磨灭的记忆事件是4月25日凌晨,被绑在市总监狱床上20小时,致使便溺全身满床。让全世界男人都感到羞辱。2003年4月24日,区政府某些掌权人,用行政手段以莫须有罪名写下了我人生最耻辱的一页。最不能容忍的是将我一个正直的公民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未告知所犯何事,强行押进市总监狱、医院。2003年6月3日,芷江西街道信访科长沉某某、顾某某、翁某某等五人将我反拗双臂拳打脚踢,全身多处青紫。2003年6月17日,我刚出小区门口,被埋伏的警察毛国良等四人扭送到警车内,押往芷江西街道软禁15个小时,被我脱身直接上了北京。 2003年7月10日,在北京接济站,上海闸北公安稳定科科长李某某、蒋亦成等8人,在床上用手铐将我反铐押往东郊民巷一处地下室内,再押往上海,13天内辗转3处。2003年7月24日被送往殷高路禁闭室,关押7天后,被送往苏北大丰农场第二看守所,开始我冤枉加屈辱的一年半的劳教生涯。我在劳教所内,吃的是泵浦菜,喝的是带虫子的深井水。暑天顶着烈日搞操练,对着太阳罚站立,寒天坐在门边遭冷冻,常常无故被打、遭电棍电击。”
“我在 2004年11月3日晚被贺等带到芷江派出所关了一晚,于11月4日送往大丰,我又重新失去自由,在零下4度的低温下,将我衣裤一件一件剥光,拿走我的鞋子,让我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每天只给我三小杯的水(糖尿病人需大量饮水)。从第三天开始每天只有一杯谈谈有浅黄色水,从专备的水瓶中倒出,入口微温。喝完感觉异常,举止烦躁不安。管教那伟等三人以心理谘询师的身份对我测试精神状况,指导员顾鲁兵对我破口大骂,说我死了不如一条狗。”
田宝成夫妇对这几年因上访遭致上海市政府的野蛮迫害经历写了近三万字的控诉材料给我,老夫妇几年里所遭受的非人性的迫害让人痛心不已。
“我去上访,想不到竟然被栽赃陷害,为了抗议政府和警方严重侵犯人权,此后两天我一直绝食,2003年4月27日我被强行上铐送到上海市监狱医院,他们将我捆绑在铁床上达9天,头部和四肢成‘大’字状,吃饭由犯人野蛮喂食。这种‘五马分尸’式的捆绑,让人既全身难受又无法动弹,这种非人折磨实该列为酷刑之一。直至5月12日我才被押回闸北区看守所,这之后承办员又多次提审我,用的全是恐吓诱供那一套,要我认罪,并讲如我态度不端正,少则劳教三年,长则徒刑十年……,其目的是吓阻我今后再到北京告状。这期间,他们为达到目的,还多次恐吓我爱人张翠平及我的兄弟姐妹,说我的罪名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这种手段卑劣之极。2003年12月2日,这本来是我被刑拘期满的日子。晚上6点许,闸北看守所一位姓朱的退休反聘狱警将我带出4号楼的逮捕间,送进了3号楼的劳教间,并口头通知我:‘你被劳教一年零三个月’,这是什么世道啊,我当即向他索要有关劳教我的书面材料,他说没有。此后8个多月,我一直被关在闸北看守所,我曾多次要求看守所拿出对我实施劳教的依据,得到的回答一直是:‘你的东西我们这里没有,上面就让我们把你押在这里,别的我们不管’。闸北分局承办员蒋亦城和刘训城等五人来跟我谈条件,他们说:‘你们夫妻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无条件投降,我们放你出去,二是坚持讨公道,那就只有蹲监狱。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11月28日,闸北区信访办主任叶明也来到看守所,他骂到:‘娘个戳×,你搞清楚,你们是自讨苦吃!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否则,关死你 ’。2004年6月22日,因闷热难忍,我拿起纸片扇凉,一位姓刘的管教硬说我不服改造,动手打我,边打边说:‘怎么,还不服气啊,你会告状是吧,去告呀!我打的不止你一个人,很多人被我打过,打你又怎么样,我下午把驻所检察员叫到你那里,你告我好了,告诉你,以后有你苦头吃’。第二天我向副警长孙国庆反映昨天被打之事,要求见所长,孙国庆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不等我讲话就一阵拳打脚踢,边打边说:‘这是什么地方,还有你讲话的权利?打你又怎么样了’。我被打倒在地,他有狠命踩,我痛得大叫:‘警察打人’,孙国庆跑到隔壁卫生间,操起一杆洗厕所用的拖把拚命往我嘴里塞,还一边说:‘我叫你叫,你再叫再叫!’我的两颗门牙当场被打掉,头部、胸口、手臂、大腿等处被打的都是伤痕。听到我的残叫后,姚所长来了,我给他看伤势,并要求做伤残鉴定,他根本不理睬,冷冷地说:‘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样的’”。
“高律师,我的孩子都和他们一般大,我像一个孩子一样被他们打的满地打滚呢!”
田宝成的老伴张翠平几年来被上海市政府的非人性迫害叙述的更多,这里仅摘述以下:
“有一次,鲁世玉、施有才等警察又闯入我家,用一种不容质疑的口气下令:你们知道,中央要开两会了,现在带你们到横沙岛散散心,你们不想去也得去。就这样我们夫妻被强行带到闸北分局做笔录,随后被3辆车押往吴淞码头。10月10日早晨,我们夫妻被警察带离横沙岛,随后我被他们单独押往闸北看守所提审。上午10 点许,鲁世玉以‘非法集会示威’的罪名宣布对我实施刑事拘留。从10月10日至16日,在闸北看守所我共被提审`19次,有时其他犯人睡觉了,警察还来提审我。提审者无一人向我告知身份,面对恐怖和威胁,我连续4天不开口,维护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和沉默权。由于我连续4天保持沉默,10月14日中午起,三个不穿警服的陌生人把我带到底楼一间约30平米的特审室后,连续28小时不松手铐,不让我坐凳子,不让睡觉,更不给我吃饭。为了逼我开口,他们竟在我面前树起一盏脸盆大的强光灯,灯的温度极高,直刺人脸和眼睛,我被烤得头晕目眩、大汗淋漓,实在忍不住时我便把脸侧向一边,警察轮番上来揪住我的头发粗暴地把我的脸推向高温强光灯。一夜下来,我的头至少有二、三十次被他们推向强光灯。这28小时中,他们换了三班人马提审我,我四次晕倒,其中有三个便衣用皮鞋踢我,骂我装死,要我起来。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他们又骂我在演戏……。那天下半夜,一个中年便衣晃到强光灯前,我瞥见他披着的警服,扭头细看警号,他慌忙用手捂住喝道:‘不要看,这件衣服不是我的,你不要到了外面瞎写。’如此外强中干、心虚胆怯,实在令人齿寒。这个中年人也是折磨我最凶的一个恶警,两个月后,他们再度提审我时,我才知道他的警号是034054。那天,三班人马对我轮番恐吓:‘你知道吗,这个特审室是专门提审那些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杀人犯的,你在这里受审,说明你的案子要判十年二十年。’我依旧一言不发,一个40来岁的便衣见我不搭腔,便无耻地挑拨我们夫妻的关系来了:‘你是外地人,而且你现在已是犯人了,你老公不会要你了,说不定他身边现在正睡着别的女人。见我仍不理会,他接着自演自唱道:‘在北京,你们里面谁是头,是谁指挥你们到这到那的,如果你隐瞒事实就判你十年二十年。一个女便衣见我始终不吐一个字,冲我发起火来:‘你这个神经病,马上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就像日本电影《追捕》那样,给你打针吃药把你变成一个疯女人,你别以为政府没办法治你,放聪明一点……’”。
在一份“沪委办发(2005)199号”官样文件中,记述了这样的政府政绩,该文件称:“……对在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先后有6人被劳动教养,17人被治安拘留,15人被刑事拘留。”但在一份由韩忠明、蔡文君、沉永梅联名给我的函件中,我看到了她们对上海市政府隐瞒“政绩”的揭露:
“且以下列被上海当局强行加罪关押的诸多上访人数来驳斥此文的伪说。
如上海因拆致贫的龚浩民(上访十年未解决)、朱东辉、王巧娟、许正清分别因到北京上访而劳教二年半、一年九个月、一年、判刑三年,至今在押。其中龚浩民还受到审讯时用强光照眼睛、冬天赤脚跑步、朱东辉在看守所被剥光衣服双手反铐悬吊三天三夜至昏迷并用冷水浇、用西瓜皮砸生殖器等酷刑。
又如上海的马亚莲被两次非法拘留、二次枉法劳教,并违法关在看守所,剥夺诉权,还在寒冷的天气施以剥光下身固定在‘凯迪拉克’刑架上三天三夜并用皮带勒内脏和呈大字型在病床上固定捆绑18天的酷刑,致整个脊椎骨变形,伤脚终身残废。现贫病交加,连生存都难以维计,更无钱治病,陷于绝境和病痛的折磨中。
上海的毛恒凤则在劳教场所被呈大字型于2004年8月9日——17日、11月9日——12日捆绑在床上,并用口罩加厚布蒙嘴、鼻,警察坐在她胸上,用膝盖顶下腹的酷刑。
再如王水珍因进京上访,被诬陷脱居委会干部的裤子,在得到市委副书记刘云耕的“重视”下,无端判刑二年。
老实、木讷的周荣华则因凌晨3点动迁组非法强拆时,在一帮民工破门而入、绑母殴周情况下,情急中自卫、救母欲以汽油浇身来吓退行凶者,并未真正实施,而以“纵火罪”被判刑一年。
上海因上访被劳教者还有吴宁、徐桂宁、戴玉英、陈恩娟、徐兆兰、刘华琳、曹仁荣、杜阳民、谈兰英、孙健、王颖、叶根生、宣雅芳夫妇、姚克健兄弟俩……,他们中最高者劳教三年。孙健、徐桂宁、戴玉英、杜阳民、田宝成、张翠平还被分别施以电棍、双手反铐吊在铁栏上四天三夜、冬天剥光衣服、夏天晒太阳等不同程度的酷刑。
而上海因上访被行政、刑事拘留甚至无任何手续拘押的人数更是众多,单因动迁上访被拘的就已达70多人(不完全统计),其中有的人还多次被拘,如无任何手续就被拆去住房而无家可归的沉永梅,已因上访三次刑拘。‘享受’非法遣送、监控、软禁者更是不计其数,很多人因此致病。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整治,并试图用针药、刑具“治成”真正的精神病。如毛恒凤、刘新娟、陆春华、张忠海(出来后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后病亡),还有思维清晰、机智、文笔流畅的张奋奋;洪玲玲则被公安局违法关进精神病院,虽经家属多次抗议、交涉,主治医生也明确目前无精神病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放;时年75岁的孙东水、金福生二位老人因抗拒非法强迁被当场强制送入奉贤县精神病治疗中心。2004年3月28日,家属突然接到孙东水单位办理孙东水后事的通知。”
又是酷刑,又是扒光被迫害者的衣服,又是攻击被迫害者的生殖器……。
我总是去打乱人们的静寂及这个社会的歌舞升平,这又是一篇满浸着我同胞的血和泪的“调查报告”!被长期的麻木浸淫着的众生正又忙碌着再过一个“盛世大联欢”的新年,夫人提醒我,这几日,许多人忙着收年礼、收年货应接不暇,大多数人正陶醉在单位发给的价以千计、万计的礼物、优惠券的快感中,“高智晟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夫人的感慨不无道理,但却不能构成我们也去麻木、去享受另类快感的理由。
是的,我们社会的许多人已习惯了麻木,有些同胞还很会麻木,诸如那位曾因激情难以自持地深揭猛批“法轮功”、“邪教”而在央视上红极一时的司马南先生就很令人刮目相看。他看了我12月12日的对中共政权血腥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真相调查后即壮怀激烈地说:“确实吗?仅凭当事人陈述能靠得住吗?”我这里是无意问及当年司马南先生是获得哪些完全“靠得住”的事实来支持他对“邪教”的批判的,若对被迫害的亲自承受者的陈述都认为“靠不住”的话,我们民族有足够多的理由再持续地麻木上它500年。
当局最近正四处疯狂打压所谓的“颠覆政权”者,杜阳明老人的一段话对我颇有些启发:“中国人民本来是最通情达理,每一次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变故后,都擦干血泪埋完尸体,衷心地感谢灾难的制造者——党和政府,耐心地等待迟到的公正——平反昭雪。年复一年,反反复复企盼着神仙与皇帝的降临,企盼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英明、企盼着针对上访潮的善政的出现,现在,我什么都不要啦,就要人权!若我今天接受了它的财产补偿,它明天就可以再抢去。我们就要一个永远不抢人的政府,抢了人,动不动就关起来迫害你!这样的制度是王八蛋制度,我们现在就是决不再要你这毫无人性的制度,现在所有上访的人都是这样,我们不要解决问题啦,就要一个把人民当人的政府!我们不怕你抓,你抓了十几次,我哪次怕过?”
自称是执政的中共,你听一听,你有虎狼若上海般的地方政府,还需要由他人来颠覆你的政权吗?
在中国,遍地都是性凶犹豺狼般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正加班加点地、疯狂地且还是认真地颠覆着你的政权!
2005年12月29日 在有便衣特务跟踪的日子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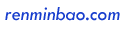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