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便是命运”那句话说得太好了。从《老井》到《中国之毁灭》的二十年间,郑义走过一条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道路。他去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掘被长期掩盖的文革惨剧。当年凶手虎视眈眈、受压者馀悸未消,搜寻屈死冤魂的踪迹决非易事。郑义和他的妻子北明却终于查明文革中广西骇人听闻的人吃人惨剧的真相,并探究了起因。他深深卷入了天安门运动,不是象某些作家那样拿著笔记本和答录机,而是站在第一线,冒著随时会被捕的危险。“六四”后他又并不外逃,而是作了一个独出心裁的抉择:在国内逃亡,在逃亡中以笔为剑“打游击”。一部手稿已辗转到国外,仅由于受托者担心他的安全问题而未能及时问世。直到“弹尽粮绝”,他们才不得不逃亡国外。流亡美国,生存条件并不象有些人想得那么好。郑义的情况虽不属最坏,也并不是无忧无虑的。然而黄河两岸父老乡亲的无言的嘱托却始终萦绕于怀,一部以近百年农民命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神树》便诞生了。其后不久,想不到他竟把笔锋一下转向中国小说家极少问津的领域。
他是不是低估了这项工程的艰巨?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苦也是他自己找来的。也许正因为这是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他走著走著,如同在广西那样,探险的精神又冒出来了。他一定要穷其究竟,这就难了。他已离中国多年,又不通外文,难以想象,这部巨作从材料到论点耗费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难怪他夫人说“先生有了一个情人”,没有更恰当的比喻了。他追求一个情人,他在太行山上和别人一起扛巨木,他在黄土高原上反复跋涉,都用过比常人更大的力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蛮劲。他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上的究真精神,在作家中也是少见的。
“血沃中原肥劲土”,两代中国作家在三十年文学的沙漠中销声匿迹之后,一代新人从这块浸透了血泪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了。郑义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九七九年春,伤痕文学写文革的作品已经不少。果真是“伤痕”,多是写文革的创伤,正面表现文革的,据我所知,首先是郑义的短篇小说《枫》。写的是一位姑娘在争夺一栋大楼的武斗中,死于她的情人所属的对立一方之手。记得一九七九年二月,《解放日报》的一位编辑拿来一份校样要我写评论时,我没写,因为觉得在当时条件下它不可能通过。可见作品的力度超出一般。想不到居然发表了,还拍成电影,不过虽然删去最后一个场景——男青年抱著情人的尸体向红太阳走去,还是禁演了。自是以后,郑义不如其他作家多产,但每有新作,读后心里都是沈甸甸的。七十年代末起,同新闻、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文学的自由幅度最大,也受到普通人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与此同步,文学和现实、和人民的距离却逐渐拉开了。郑义却不改初衷,这才把自己引向这部《中国之毁灭》。
书中陈述的很多事实,中国人都身在其中,并且就是它们的制造者,因而并不陌生。然而噩梦的碎片毕竟不是噩梦,何况剧中人往往就是自己!局外人也至多在瞬间略感不快;碰到的次数多了,还会习以为常。甚至在制造砒霜而人畜中毒、土地寸草不生的地方,人们也能自得其乐。连这些人,意识里都不会出现“毁灭”二字,遑论他人?《中国之毁灭》里说的是一场正在逼近的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作者第一个向国人展示了它的全景。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有导致一些国家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死亡的欧洲十五世纪的黑死病能够与它相比。郑义的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中国人,你无处可逃了!”
也不是没有出路可寻,虽然大劫难已难以避免。
人口过多而又急剧增长,已经造成了一个定势:为了今日的生存,就必须破坏明天的生存条件。长达一个世代的无权、无望和无自由状态,加上贫困和蒙昧,从精神和物质上为人口的无限度膨胀提供了新动力。那几十年,男人除了使女人生孩子,还有什么自主权?生殖又是发挥人类生而有之的创造性的唯一天地;性交成了劳苦无涯生活中唯一的享乐。何况一个新生命还能让大人分享他那份口粮呢!人既无知于生命的价值、也无力于保护自己,无意于对他人和社会承担什么责任。而一当富裕,便从动物性生存境遇走向另一极端,穷奢极侈。资本主义在英美始于勤苦,而当中国于二十世纪末再次引进资本主义时,它却已处在必须靠高消费维持其生存的阶段了。这是同我们的人口与资源条件全不相容的。十几亿人口(注)这一个事实,就决定了中国人必须甘拜下风,节制自己,承认自己无权像美国人那样消费——且不说美国那样的消费也将遭到报应。而今天中国的权贵和富人,还忙不迭地向美国看齐,恨不得把沿海、大城市同内地切开,能变成新加坡那样一个孤岛也好!只求经济增长,或只要一个多党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怎么样?)而不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存问题、又可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的独特道路;不使国人摆脱消极、敌对心态而自我动员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变自己,一切都无从谈起。而眼前的现实,却是把人和社会朝相反的方向推动。根本的问题是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从而使他们对社会总体及自身的态度有一个根本变化。
同郑义相比,我要幸运得多:比他年长二十多岁,无病无痛,傻吃痴睡,简直无法想象他在几种新旧病患交错袭击下,五十万字的著作是怎样写出来的。只知道他在电脑前,常常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用尽了各种姿势躲避病痛对他打字的干扰。要有多大的毅力,才能使文思不致瘀滞,神志不致涣散呢?同时,这些年他又把多少精力用于为海外民运而奔波、而焦虑!尽管如此,郑义仍然是流亡者中十年来成就最大者之一。
我和郑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但这不妨碍我们仍然是朋友。我为他的这部划时代的力作之完成感到振奋,愿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一读,认真地思索,广泛地传播,继之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为了中国,为了世界!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于普林斯顿
(注:根据日本政府厚生省按人均食盐量的调查和统计,中国人口在一九九七年已达15亿。较之中国政府的统计,我更相信这个数字。那么四年后的今天,又该是多少呢?不详。故只能含混称为“十几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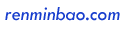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