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唔唔唔(嘴中有饭),蒋夫人毫无影响。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年这事开始时,我们就没说要把蒋先生怎么样。因此后来我与杨虎城俩几乎闹翻了,就是为这个事情。杨虎城怕了。我说:“咱们当年是怎么说的?如果你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反对内战,你是不是又惹起内战?你不是扩大内战吗?你为什么自己做的事与自己心里的愿违呢?你既然要怕,你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你不用怕,我去负责任就行了。”我去南京时,我真决心去死啊!那南京可以把我枪毙啦。我自个儿说:“我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毙了。”
郭:老先生对你还不错啊!
张:那是,不是他死后我写副对联吗?“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重新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还是关心。这里我还要说,那后来经国先生对我更好了,对我好得很,对我很关切。不过当然啦,政治上问题是政治,私人感情是私人,我那天不是讲,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就像九一八那不是政府,那是我的责任,我这个人是这样。
郭:如果您这一生重新活过?
张:什么?重新来过?我九+岁还重新来什么?明年也许完蛋了。 我有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
张岳军总骂我那两句。我就是虚名害了我一生,我不是谦虚,我自认失败,一事无成两鬓斑。
虚名害了我一生
唐:汉公,在我们学历史的人来看是成功啦,成功,是不能看短期的。
张:我给自己下了个考语,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啦!
郭:汉公,我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向您这老头子致敬哪!
张:怎么地?你要拜我做老头子?我又不是“青红帮”。(对唐指郭)他说拜我做老头子,我说我又不是青红帮(张开玩笑,因老头子在青红帮是老大的意思。)有一首诗我倒想告诉你,我在谒延平郡王祠时有这首诗:
“孽子孤臣一(禾犀)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我最得意后面两句,你看出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
郭:您是在讲蒋先生?
张:在讲我自己啊!讲东北啊!
假使我不这样子的话,东北不是没有了?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就是土肥原顾问的“王道论”中说明了,意思是不要我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捧我帮我。我为这事跟他火了,我以后就不见他,日本没法只好把他换了。
我父亲死后日本派元老林权助来吊丧,事后我请他吃饭,他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这里,我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代啊,意思是不要我挂青天白日旗。我说你忘掉我是中国人啊!我这是喝了酒有点失言(意思太不给林面子),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我去送行时他的随员还想跟我讲,他制止他们,我也知道东北危矣。
郭:有人说其实您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情况会较好,对您也较好?
张:那当皇帝?
郭:这可能对东北比较好啊?没九一八,东北能保持现状?(郭在激张)。
张:为什么我要服从?我就变成日本傀儡了?!
郭:可是您有实力啊!东北很大啊!
张:东北是大啊,但你不知道,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要怎么就怎办!你这问题问得根本不懂情理,我为什么责备你不懂情理?我父亲怎么死的?我先问你,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
就是不做日傀儡
郭:就是他不合作嘛!
张:他就不给他当傀儡,明白这话?你要做,就得当日本傀儡。日本是对你好吗?他要侵吞你啊!我后来跟日本朋友说笑话,我说你日本人不能叫人跟你合作,就像我有老婆偷你人,你别作声,咱们也就算了,你呢?你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老婆跟我睡觉,你日本人就干这种事。你跟他当那傀儡还得像一个傀儡样儿啊!所以你说我责备你,给日本当傀儡也不好当啊!
郭:可是有人说大帅(张作霖)如果在的话,大帅不会跟中央合作啊?(即大公报评张说:“其操卫则大逊于乃翁。居历史事实积重难返之地域,乃以国仇家恨,著之颜色,形之文字,于是日本视张为不并立,而渖阳之变起矣。”)
张:那不一定,那就不知道,这句话也有道理。所以我说日本人混蛋,我父亲愿意合作都被杀,那何况我呢?也许那时我父亲比我容易操纵,他们都不容,他们没想到我更难搞。我今天九+了,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说这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样子讨厌。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就连杨宇霆(后被张杀)也没想到,他也想操纵我,换句话说,我这个人不受操纵的。就连蒋先生想操纵我,我也不受操纵的。我要受操纵还有今天?我有自己主意,我有自己见解,那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个样。我那时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自己。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就是一件事,他是行政院长,同宋子文到北京来看我,拿了蒋先生一封信,他的主意要我们与日本打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我说汪先生您说什么?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你那么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有信是让你跟我商量,如果蒋先生,军事委员会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我就打,我非服从不可。但要我自己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否则我不干。他一怒回去就为此事辞职了。
反内战反对透了
以前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都是为中央统一,所以我说阎百川
(阎锡山),他那时就没想到我。我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我有这个意思,你不听,我打你,中央要是不听,我就带你打中央。你明白我意思?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我父亲后来不打(出关)也是我。我给我父亲痛哭流涕啊!我从河南回来,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因前面有红枪会,我火车停在那。我看到这事情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在车站看到那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饿的。我把馒头扔给她,给她钱都不要啊,扔给她,她放在地上连土就抓起来吃。我说怎么这样?我就问她,你没子弟吗?没儿女?她说都给抓当兵去了,拉去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饿得没饭吃,这怎么?年年打仗。我自问,谁做的孽?自个自个儿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和,后天又不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无能后备的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种战争干什么呢?我父亲看我激动,教我不要打,休息几天,我痛哭反对啊!
唐:你在河南作战后是否留了封信给北伐军?
张:那封信我是留在陇海铁路司令部给前线的北伐军,好像是白崇禧。信很长,我还记得,我告诉几件事:
第一,我剩下粮草我可以放火烧的,但用来赈济老百姓我不烧。
第二,我说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上来,我把它毁了你们一时修不来,我没炸因为这是国家的桥梁,我没毁。
第三、……(忘了)
郭:您是否有说大家干脆不要用军队打,有种拿手枪比比算了?
张:他们不敢的,嘿(笑)!这是为什么呢?真有目的还可以,打来打去,我真是厌恶,我一直厌烦这些,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我不愿意剿。有什么意思呢?
唐:自己打自己。
张: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我跟你说个小故事,张发奎你晓得?我跟他在河南打得非常惨烈,他号称‘铁军’,双方死了好多人,到后来在英国,大使郭泰祺说要给我做介绍,我说我们早认识啦,不打不相识呢。后来我们很熟,还在红宝石酒楼一起吃饭。
郭:谈谈您四弟张学思,他是不是在溪口书房中与您笔谈?
张:是这样的,那时我四面都有人(监视),我们也没谈什么正经事。他写说他是共产党,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书,那不是正经书(意思是要看马列)。那时候他很厉害的,他说他在军校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怎能不败呢?内部好多人都投了共产党。他本来毕业的时候我推荐他去胡宗南那边,他没去,就跑到东北军去了,在东北军中鼓动得很厉害。东北军后来投去共产党那边很多,最厉害的就是吕正操。
郭:东北后来掉到共产党手中,有人说中央不放你回去,张学思去鼓动等都是因素?
张:嗯嗯,后来文革时共产党四人帮说他是东北帮首领。把他整死了。
郭:周恩来对张学思之死一直很难过痛心?
张:兄弟中我最喜欢这个弟弟。我从前跟你说过这话,我宁给好汉牵马蹬,我不给赖汉当祖宗,你懂这话?我这弟弟有骨头,我那二弟(学铭)我就骂他色大胆小。我这弟弟最有骨头。
郭:来到台湾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老先生?
张:我说不出来,(他)在大溪住的时候。
郭:他找你去的?
张:他不找我去我怎么能去?
郭:他对你讲了什么?
张:我不告诉你。
后来见过两次,大部分都是经国先生与我见面。我与经国先生很好的,我们是无话不说。
郭:那封“忏悔录”是怎样呢?
张:那是老总统要写“苏俄在中国”,他怕写错了,就叫我把西安事变写下来。他说:“我这方面的事很清楚,但他们(共)那边的事我不清楚,你可把它写下来。”我说:“西安事变我本是至死不言的,你今鞠诚问我,我就鞠诚对答。”后来写了,不知是谁,大概是王升都不一定,反正是经国把那信改了,信头改了,把它掐掉了,要我拿回来,我重新给他写过的。这稿子我还留著,他拿回去就发表给将领看。后来这事出了很多波折。我看到了说,如果你写“张学良忏悔录”,我不能说什么,但他写了“忏悔录”,不署名张学良,好像这东西是我自己发表出去的。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并不是说我反对,而是说蒋先生可别误会是我发表。蒋先生火了,所以把办事的撤掉,东西也收回来,就这么回事。
蒋当然已原谅我
按:忏悔录应在民国四+四年所写,当时经国先生尚未奉命与张学良多联系。老总统看了最出意外的是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张要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张个人的决定。第一次写的,蒋非常不悦,对著监管张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大骂张学良说:“他还不悔过,国家到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他知道不?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刘乙光儿子刘伯涵转述)稿子也退回改写了,是赵四小姐抄的。
张: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因为他确实知道没人帮我忙。他说你怎么会写这么好的文章,他后来叫人来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我本来写了一点后来就不写,后来他也不过问,我说过,高兴写不高兴写没有心。
唐:您觉得蒋先生原谅您吗?
张:当然是,不原谅?他把我枪毙了。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我不在乎,真是不在乎。我就是今天还是敢说这句话,当著你们三个人:假如国家要用到我,虽然我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事我不干,假使那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干。
(博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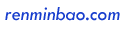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