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领导人尽管被他们自己、御用文人和一些奸佞小人捧上了神坛,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其实不用卸装,谁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皇帝新衣”里面的草包模样。仅仅是由于中共尚未垮台,还握有军、警、司、特的生杀大权,许多人不敢讲、不肯讲或不屑讲“其实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这类真话罢了。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打江山时大多是一些土匪、强盗、毛贼,其中还不乏“一把菜刀闹革命”和“双枪老太婆”之类的杀人犯、山大王。后续的一些领导人则是一些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和献媚小人。他们在中共这个大染缸中凭着吹牛拍马、告密诬陷、整肃异己,不择手段地踏着别人的血迹,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记得“6.4”前江泽民还只是一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与中央极权的小圈子相距甚远。当时乔石的一位亲戚来沪治病。江泽民不但亲自安排他住到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指定最好的专家给他诊治,而且还亲临医院探望,派卫兵严加保护,搞得华东医院人仰马翻。非但如此,江泽民还亲自毕恭毕敬地送花到病房,请求他把江泽民恭贺乔石荣任中央常委之意转告乔石,借以向乔石输忠。但“6.4”后,江泽民大发利市,直窜中央,乔石则反被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高位上步步逼退。这是江泽民与李鹏作了台下交易的结果。“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真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绝妙写照。
既然是流氓,一旦爬上权力顶峰,最拿手的自然是实施其流氓政治。虽然迫于世界大势,土流氓变成了洋流氓,中山装、军装变成了西装,但本质不变。有心人若将毛泽东谩骂梁漱溟、邓小平下令“6.4”开枪、李鹏威胁“6.4”学运领袖、以及今天江泽民痛斥香港记者的镜头放在一起欣赏,马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共同拥有一副“共记”政治流氓的丑恶嘴脸。
江泽民虽然大言不惭地对华莱士自称“我也是选举选出来的”,但是,谁都知道,他是由邓小平钦点的,是邓小平和陈云谈判妥协后产生的政治怪胎。江得以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青云直上、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要原因是:他在“6.4”中坚决取缔、镇压了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因此,江泽民的新顶戴也是用“6.4”死难者的鲜血染红的。这也正是江泽民在国人皆曰可杀、国际舆论一致声讨声中,硬着头皮力排众议、死挺李鹏的主要原因。
可惜,流氓就是流氓。尽管江泽民再穿上量身定做的西装,戴上高贵的进口领带,忽而吟诗题字,忽而弹琴唱歌,忽而来上几句现抄现卖的英语和蹩脚透顶的广东话,自我陶醉在“谈笑风生”的王婆梦中,以为就此可以博世人一笑,忘了他是个流氓,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流氓就是流氓。流氓再作秀、扮绅士、装傻笑,也终究还是个流氓!如同毛泽东在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一书中被剥光画皮露出了流氓纹身一样,江泽民在教训香港记者的3分钟镜头中,也活现了一副流氓新教父的本相,令人侧目。
笔者不幸与江泽民有过两次间接的交锋,因而比这些香港记者早17年领略到这个政治流氓的淫威。在劫后余生流亡美国的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写下这段真实的经历以飨读者,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笔者因78、79年在上海人民广场民主墙上张贴了72篇杂文并创办民间刊物《科学民主报》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莫须有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1985年,江泽民还在上海市长任上,市委书记是芮杏文,而我则正在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场2大队服刑。我的女儿张冰(目前正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研读法博士),当年只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初中学生,由于父亲入狱,母亲病重,家有覆巢之虞,16岁的小姑娘在走投无路之余,某晚忽发奇想,流着眼泪给江市长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泽民”一下,考虑允许我保外执行以照顾濒临破碎的家庭。这本来是一封极其普通的“人民来信”,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所谓“保护”的。至于准或不准,当然决定于当权者。却不料江市长竟因为我女儿文笔老到,又对信中请其“泽民”一言大为震怒,而毫无根据地认为此信是身陷囹圄的“反革命”父亲幕后操刀的。
于是,在我服刑的白茅岭劳改农场2大队2中队,就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搜查。由于我这个“反革命份子”尚有一技之长,故在白茅岭劳改农场中担任了建筑预、决算、制图、放样、施工、安装、筑路等技术工作,还拥有一间独立于集体牢房之外的工作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警校毕业的2中队副中队长王旭明突然带了大批警员前来抄监,对我的工作室和监房实施地毯式搜查。就连我精心收藏在一本笔记本夹缝中的、一位台湾难友张靖雄的地址,也被抄了出来。这张小纸片曾经逃过了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的道道检查,在笔记本夹缝中隐藏了多年,最后竟也难逃罗网!最后,要不是老中队长竭力保我,以及工作上少不了我,恐怕我早已被打成“反改造尖子”而加刑流放到塞外荒漠中去了。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搜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数年后刑满获释,我才从女儿处得知了这件乌龙事件的全部真象。此时,对一封普通人民的来信如此神经质地大动干戈的江市长,早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了。
1993年,为了抗议上海市公安局将精神正常的原上海工自联召集人王妙根强行送进警方的精神病安康医院长期关押,我决定在上海人民公园召开“6.4”4周年纪念会。结果是:我再度被捕下狱。我未经审判便被处了所谓的“劳动教养”3年。警方甚至赤裸裸地威胁我,逼我放弃上诉,以换取我女儿赴美留学的出国护照。在“劳动教养”期间,我偶从报上看到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利斯多弗时,针对美国的人权压力,竟然把采取和平抗议手段的中国民运份子无端地诬蔑成“企图推翻中国政府、制造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人”。为此,我在给一友人的密函中痛批了江的论点,认为江可以和国民党“相逢一笑泯恩仇”,可以和小日本握手言欢,唯独将民运人士当作假想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在转递过程中此信遭警方截获。据处理此案的上海劳教局管教科长李兴豪亲口告诉我,此信已送达江泽民手中。江泽民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曾两次到上海亲自过问我的严管措施,饬令封锁一切可能的传输管道,不允许再有片纸只字密递出狱。从此,我就被关入严管队密室,被抄走所有的书刊、纸笔。3年中,狱方将我陆续转移了9个牢房。冬天时,他们把我丢入无门无窗、只有铁栏的破监房中。夏天时,他们把我丢入密不通风、闷似铁皮罐头的牢房里,使得我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心肌劳损、高血压、糜烂性胃炎、牛皮癣等10多种疾病,且长期过着无书无报、无纸无笔、无医无药的悲惨生活,险险乎病死狱中。最后在国际大赦等人权组织的不断声援下,我在被关押了3年多后,获释流亡来美,但却留下了许多终身不治的后遗症。拜江泽民所赐,我至今还在忍受这些病痛的种种折磨。
因采访我而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的法国《解放报》记者富兰克林,在获悉朱镕基升任国务院总理后,曾经兴奋地打电话到大陆来询问我:朱镕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类似戈巴契夫的“黑马”?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从自己亲身的经历,非常了解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这些中共第3代领导人的流氓本性和残无人道。近来江泽民对中国民主党人和法轮功学员的野蛮镇压,和朱镕基一边在电视台与日本观众进行柔性对答,一边却恶狠狠地祭出国防白皮书威胁要对台湾动武,就是极好的佐证。这些政治流氓为了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已不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江泽民在教训香港记者时,气急败坏地连什么“闷声不响发大财”的心底话也脱口说了出来,因为,江的儿子江绵恒正在继邓朴方之后大发横财、鲸吞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成为中国的新贵。而江、朱、李这三头马车,正在策划如何把中国的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全数转移到海外。为此,他们不惜挑起一场以任何借口发动的、针对任何一个假想敌的流氓政治战,来祸国殃民、乱中劫财。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纳粹集中营里如是说。(2000年10月28日于芝加哥)--摘自民主论坛(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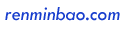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