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东北地区拉广告,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五年来,我一直坚持把新闻报导放在第一位,这有违于港馆领导的大政方针,在总编和社长看来,《文汇报》应当环绕着经济效益,去找新闻,或者确切地说,是先去吹捧某些企业,或某个官员,再去伸手要钱,只是报社领导不主张来硬的,而是用软的,用交朋友的办法,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至于付面报导和突发事件,向来是报社领导慎之又慎的问题,前者一般不碰,后者实在绕不过,就粉饰太平,颠倒黑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作为十几个驻地办站的负责人之一,绝对是人微言轻的,一来我不是广东省委八办的在编人员,二来东北经济实在不景气,没有珠江三角洲那么多有钱的企业,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在《文汇报》都无足轻重。不过,有趣的是,在港人看来,东北是不毛之地,治安环境很糟糕,总有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在那里,如果当事人涉及港台,就成了热门新闻,故此,我又每每身处舆论的漩涡之中。
记忆里的许多重大的突发事件,都在我的任期冒出,也都与东北有密切关系。比如, 1998 年轰动港台的林滴娟命案, 1997 年的 钟少雄绑架案,1999 年的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贪腐案,哈尔滨副市长朱圣文贪腐案,等等,此外,还有黑龙江的洪水,山东烟台的沉船,漠河的日全食,总之,如果现在翻翻《文汇报》,可以看出我对类似事件是花费很大气力去报导的,大都是第一时间,和第一手材料,所以,主管报导的副社长王伯遥对我评价很高,他对我的林案报导的评价语是 “领先一步,好评如潮”。
然而,令我最悲哀的是新闻真实性的问题,很多报导是做到了这一点,但还有大量的保留,比如,花钱买凶杀害林滴娟的是李广志,李是一个在辽宁海城做镁矿生意的商人,他的后台是他的父亲李某,而李家父子的后台是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李力践父子,李铁映在海城任职多年,与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时,有知情者透露,元凶李广志就是在李铁映等官员掩盖下逃跑的,至今没有规案,杨荣喜不过被利用的杀手和替死鬼而已。
还有钟少雄案,他是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他的父亲在鞍山搞内部股票骗了不少人,当地黑社会派人把他从广州绑架到鞍山,其目地是父债子还,我是通过总社记者王坚第一时间知道这个线索的,随后我驾车飞速赶往辽宁鞍山,由于我在当地和黑白两道的人都有关系,很快查找到了钟少雄被绑架后关押之处,所以,我发表了非常有现场感的一篇人物专访,在香港轰动一时,也促成了钟少雄的尽早获释,但依然有所保留,有知情者透露,绑架行动是由鞍山某公安人员操控的,连市政法委书记张家成也身陷其中,后来,我坐牢时,他当了省司法厅长,有一次,还带领监狱管理局长,到我所在的大连南关岭监狱视察,竟装着不认识我,如果,我当时披露了全部内情,他后来不会有高升的官职,想来苍海桑田,人心难测,真是后悔……
至于慕绥新案,马向东案,朱胜文案,等等,都颇为类似,总之,当时我的处境,虽有一份勇气和担当,但由经济地位所决定,为了生活的物质条件领先他人,不得不在报社领导的要求下自律,平心而论,编辑部不会对某一个细节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报纸政治背景的整体框架制约了每一个人,久而久之,不用报社高层讲话,我自己就知道适可而止,这种情况,海内外的媒体,只要是中共操控的,无一例外,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公平地剥夺了读者的知情权,而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导致的行动,就是茫然轻率的。
总之,我得出的结论是,《文汇报》身处“一国两制”的香港,他所有的新闻报导都是一半真,一半假,究其原因,不是老总和采编人员心无明镜,而是大家都是凡人,都为了一碗饭,没办法,根子还在上面,在于国家的领导体制。
半夜里来了新娘
正因为一党执政,一个强权操控媒体,舆论只能讲好话,所以,长期以来,使《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媒体,在东北成了香饽饽,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论到哪去采访,都受到基层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接待,特别是中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拿 1997 年百年一遇的漠河日全食来说吧,那次采访的经历就满有趣的。
我从大连乘火车晚上出发,要耗费一夜时间,第二天凌晨才能赶到哈尔滨,然后,再转车去黑龙江省的西木林,它是一个很小的车站,离中俄边境的北极村很近,日全食的最佳观测点就在它所在的漠河县,我大约历时二十几个小时,才抵达了那里。
记得那时有多家媒体同行一路搭伴,《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华大珍也身在其中,她非常有交际能力,又熟悉地方情况,故在漠河很快找到了下榻之处,但我没有办法。因为云集的官员和媒体记者很多,仅有的两家宾馆已人满为患,我站在漠河宾馆走廊里,举目无亲,手足无措。不过,当地群众对新闻记者很好,有一个宾馆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香港《文汇报》的,十分新奇,她大约五十多岁,有一张圆脸,红扑扑的,我发现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脸蛋,大概与风吹日晒有关吧!她认真查看了我的证件,想了想说,天快黑了,气候又零下 39 度,你到我家住吧!
我别无选择,明天报社要发当日新闻,最好能有日全食的照片,我必须先安顿下来,于是,我随她走去。原来,我很幸运,他的女儿刚结婚了九天,有另一处房子居住,它位于一个千篇一律的鸽子笼式的民宅的二楼,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张板床,和一个沙发,一个梳妆台,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她把我介绍给女儿,她大约二十几岁,有非常美丽的面容,和偏远山区人特有的纯朴,她说,你别嫌弃,也别害怕,就在这里住吧,我和爱人到我妈家,没人打扰你!……而且,凑巧的是,他爱人是开出租的,正好我也要用车,这样一来,什么都解决了。
那时,电脑没普及,发稿要用传真,但小小的人口两三万的漠河县邮局,只有一部公用的机器,于是,我先在这个民宅里写稿,再用电话口述给远在大连的同事,她打印后发到香港,故十分便利,我既没有挨冻受累,也免除了邮电局门前排队之苦。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我根本不能出门,读了一会徒步行走英雄余纯顺的传记,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房门忽然开了,我吓得从沙发上滚到了地下,问:谁?……没想到是新娘。房东女儿抱着一个暖瓶走了进来,她是来给我送热水的,她说,天气太冷了,我妈不放心啊,说别冻坏了记者……接着,她发现了问题:你为什么不睡在床上,我告诉她,他们的新婚被子上有一对刺绣鸳鸯,很是漂亮,被子是喜庆用的,这里没有洗浴设备,我可能身上不太干净,就不好意思掠人之美!……她笑了,问我“掠人之美”是什么意思,并说你们香港人就是这么文诌诌的,我说,我家住在大连,只是给《文汇报》打工,并非香港人,她竟说,大连是“北方香港”啊,不一样吗?……
此后的几天,我就一个人,住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小县城里,住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有几次进进出出,不会用她家的钥匙,我就随便敲开旁边的一户人家,他们也不问我是谁,就帮我开门,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比如,香港,深圳或者大连,都是难以想像的奇闻啊!
后来,我在狱中闲着没事经常回顾以往,颇多感慨,我想,这里的人民太好了,如果中国是民主体制,媒体没有捆绑,完全放开,《文汇报》能做许多回报人民的好事,而不仅仅是报导自然状况啊!
阳具拔不出来了
1998 年,台湾民进党议员林滴娟死的太惨了,她生在台北,却死在了辽宁省海城,我是亲眼看过她尸体的记者之一,当时知道她死讯的人很多,但同一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却被封锁了消息,没几个人知道,那就是,被掩埋了的旧闻:当众多台湾记者,蝗虫一样云集小小的海城宾馆之时,当地邮电局和税务局的两个领导,闹出了惊天动地的桃色新闻,前者是女的,大约四十多岁,后者是男的,已年过半百,他们先是工作上交往,慢慢久了,关系演变了,成了秘密的地下情人。
这种婚外情在东北十分普遍,对官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很多官员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百姓亦见怪不怪。问题是,正赶上海内外媒体聚焦海城的时候,有一个高档生活小区的保安却发现了异常现象,有一辆进口的豪华面包车开进了车库,连人带车再也没有出来……原来,车子是税务局某局长的,那天,他下班后带着情妇去吃饭,喝酒,吃完了又去唱卡拉 ok ,唱到半夜,最后又去洗浴,玩够了,两人缠绵悱恻,意犹未尽,就把 车子开进了车库,在里面又温存了半天,不想,车库和车里都打了空调,他们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窒息而死……
据知情者披露,当保安找到他们时惊呆了,一男一女,相拥而眠,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且,人们无法把他们僵硬的尸体再分开,男的阳具拔不出来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人们一笑置之,偏偏他们是局级干部,很多人在电视上熟悉他们,而且,双方配偶知道此事后均很生气,都拒绝收留尸体,料理后事,不巧的是,他们的尸体与林滴娟的遗体放在同一个医院里,只是分在不同的太平间。一位当地官员对我说,求求你,千万别告诉台湾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他们要是知道了,会和林滴娟的事一起炒,更骂我们共产党腐败啊!我心想,林滴娟之死,如果不是官商勾结,社会治安太坏,她怎么能死得这么倒霉,也这么凑巧呢,还和官员的性丑闻发生在同一天,这是偶然的吗?
陈县长与他干妈的纠葛
萝北县是黑龙江省一个归属鹤岗市的小县,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它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在它的北面一江之隔的是俄罗斯的阿穆尔捷特,据说每到夏季,很多美丽的妈大姆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成了目力所及的西洋景,故此,近年来,萝北县“光□岛”(即“情人岛”)名扬天下,游人如织。
不过,我常去那里的时候,是 90 年代中后期,它的知名度还不太高,我是被邀请去专访县长的第一个香港记者,官员们还是第一次知道了香港也和上海一样,有一家《文汇报》,我向他们解释了半天,他才确信这是共产党办的报纸,于是,酒足饭饱,他们看我很豪爽,就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的前任是土生土长的鹤岗人,时年四十出头,从基层的老农民慢慢地一步步爬上来,当上了县长,那几年,上级下令全力以赴招商,他就热情地接待所有的有头有脑的人物,有某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她气质高雅,举止不凡,不仅带着瑞士名表,而且还穿着一身名牌套装,其助手是个能说会道的女大学生,她在酒桌上显示了海量,趁酒酣耳热之时,介绍她的老板说,她是李嘉诚的妇人,掌管一家金融公司,正准备找一个上亿的大项目,做点生意,县长乐得合不拢嘴,就建议她投巨资改造“情人岛”,那小岛位于中俄之间,上面长满了扭在一起,全都两个枝干的情人树,李妇人听了很感兴趣,就提出立即考察,县长以为做梦遇上了财神爷,就当即放下其它工作,陪她们环岛考察,少不了吃喝玩乐,极尽地主之谊,反正花得都是公款。
他们很快签了投资协议,第一期由港方投资 3000 万元谘询开发费,县长乐开了怀……此后,李妇人又来过几次,县长拜她当了干妈,但她说,李嘉诚出差没回来,投资款没人签字,告诉县长别急,干妈的话岂能怀疑?他又热情地留干妈住在宾馆里,正巧她感冒生病,说要先到欧洲休息再回香港,走时匆忙,身上钱不多……县长慷慨地借给她十多万元,她说回头就还给干儿子。不料,她竟一去不回……
我问:你说的县长,为什么连李嘉诚的家事都不知道啊!领导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很偏远很闭塞的,如果那时,你这样的香港《文汇报》记者多来一些,多给我们宣传宣传,就好了!来得人多了,信息流量大了,就不会上当受骗了。我想也难怪, 1994 年 11 月,我去大连市外经委办理《文汇报》驻地办事处注册手续时,工作人员从未听说《文汇报》,还以为我们是特务,是反动报纸呢!她把消息第一时间报告了安全局……我问这位领导,后来呢?
他说,陈县长报了案,公安局的确很厉害,很快就在新疆抓捕了李嘉诚的假老婆,原来,她是新疆乌鲁木齐一家毛纺厂的退休工人,和县长一样,连香港都没去过,但却能欺骗共产党的干部。类似的故事,在我任期听到了很多,查证属实的也有大把,这只是苍海一粟,我想,这主要是中共长期以来操控媒体,愚弄百姓造成的恶果,而每一件坏事最后均必将反害其身,自食恶果。
2011 年 1 月 13 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转自: 香港《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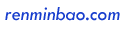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