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发生十七年之际,我们再次看到了仍然是十七年里一陈旧习、始终不变的两个沉重,继杀人凶手们的依然的蛮横,依然的冷血,及依然的不通人性。而另一个更加的沉重的存在则是:包括那次屠杀的受害者在内的、相当一部份人的、长久以来一贯地要求中共为“六四”屠杀平反的呼声。
前阶段和几名瑞士朋友一起聊天,在谈到当下国人的精神状态时,他们中间的一位可被称作是中国通的人问我:“高先生,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突然宣布解除报禁,你想中国人会怎么样?”“你以为呢?”我反问之。“一旦中国政府解除报禁,中国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很大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对中国政府废报禁行为本身的赞美方面,而不是对它长期控制人的言说自由的不合法及不道德的批判方面。人们同样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小心翼翼地,看着权力的眼色行事,你相信吗?”他继续说: “在专制中国,来自政府的,最初的对人们的强制和禁锢,早以成功地转变成每个个人内心的对自己的强制和禁锢。”他不无得意地回答。
我想,一些同胞听了上述出自一个老外的这番言论的第一本能,又会是他的民族自尊心问题,这种家丑不外扬的自尊呵护模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成为专制文化能量的滋补源。我们无法回避在今天的中国,由于这个经常杀人,且因经常玩“平反”把戏,而使它永远“正确、光荣、伟大”的中共,长期地、野蛮地恐怖压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长期以往,人们既丧失了原本既有的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等的简单判别意识,且变成了冷漠但也是很顺服的动物。当然,这种顺服仅仅针对强权的暴力或利诱,对于弱势群体的呼吁,他们是毫无顺服可言的。
中共是十七年前那场冷血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它就是那场大屠杀的杀人凶手。现在人们要求中共给“六四”平反,这也包括许多那次屠杀的受害者及其亲眷。人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这是在做什么?我们这可是提出了让杀人凶手给被它杀害的人进行平反的这样一个要求。细细思忖,这样的要求本身即是多么地悖逆基本人伦、基本情理及人类是非判断的最基本常识。
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两个自然人之间,一则,也断乎不会出现这样荒谬的情形,即便出现,我的上述批评言论也会得获得一边倒的支持和喝采。但同样的情形,若要用在人民与中共官方讨论方面,这种情形就会变得大为不同。原本应当是彻底的理屈词穷的领域,一旦有中共的出现,人们竟能将这种理屈词穷变成辩词滔滔,让人感到异常的无奈和沉重。
中共是“六四”杀人的凶手,杀人凶手是断无资格来为被他杀害者进行平反的,这大概是人类亘古以来再简单不过的伦理常识,中国人也不应该认为我们就具有了颠覆人类普世人伦常识及真理的资格。相反,我们有绝对的权力、伦理力量来催逼杀人凶手承认杀人有罪这样的人伦天理常识,让杀人凶手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样的常识价值来承担因其非法及错误杀人而所应承担的罪责--即中共应在“六四”的问题上向中国人民谢罪,依法惩办所有参与那次屠杀的犯罪人员,对所有因“六四”而受到伤害的人予以赔偿,作为其承担罪责的诚意及硬性条件,中共更应立即结束一党专权这种随时都会再出现杀人暴行的反文明的专制体制。不结束一党专权的反现代文明的制度,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成为空谈。
人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共不仅不具有平反“六四”的道德及法律资格,另一方面,他的生命机体里根本就不存为这样事件平反的功能。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历史上,干出了数不清的伤天害理的罪恶,“文革”十年之后所谓“冤假错案”的平反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背景:被打倒的、被伤害的对象后来获得了操控中共命运的能量,他就是制造“六四”屠杀事件的刽子手邓小平,他有着为那个打倒和压迫他,以及造成他长子邓朴方终生残疾的运动进行重新评价的现实性的个人本能。该运动与其说是顺应民心,不如说是延续中共罪恶统治的政治手段,,因此这场从目的上就决定了不可能维持彻底和公平地纠正罪错的平反成为中共统治历史上的异数,而非系由中共的纠错机制使然。而邓小平对于他所执行的“反右”斗争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平反,把一个55万人划成“右派”的运动说成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并留下90万余人不予平反,以此证明这个扩大了5700倍的“反右”运动仅仅是个错误而已。而今天掌控中共命运的这群人,几乎都是“六四”屠杀事件的受益者,更有一些人还应是“六四”罪责的承担者。要向这些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要求本身既是与虎谋皮。
要求作为“六四”凶手的中共来平反“六四”,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不可能,还因为它没有这种道德法律和资格。从中国民族的长远利益看,由中共来平反“六四”是对中国民族久远价值的又一次巨大伤害,这无疑将再次耽延中华民族摆脱中共罪恶统治灾难的机会及期限。中共的存在,才是所有灾难的根本性根源,“六四”灾难仅为其中之一。这一灾难当然是给我们民族造成了永久性的伤痛,尽快结束这样的灾难当然是一件民族的幸事,但结束这样的灾难模式却并非仅限于为“六四”平反。时至今日,事到今天,人们当冷静思考中共在其暴虐史上的所有运作规律,人们持续地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到了一定的危机时期,它定会通过它惯用的铺天盖地的欺骗把戏,将平反“六四”的过程营造成大规模的、使其罪恶声名持续获取恶能量的过程。它不但又会大呼这是顺乎民意的“先进性”本质,同时又会告诉人们那是它有错必纠的历来伟大。这样的、由中共来完成“六四”平反的过程,不仅是违反人类迄今拥有的普世法理共识的过程和违反人类道德共识的过程,同时这样的过程将会被历史的证明是一次加重我们民族历史性灾难的过程,这是我们必须谨记的。
我们理解那些在中共持续的暴虐统治面前已没有了提出尖锐问题勇气的人们,但我们却绝不原谅那些因恐惧而自己丧失、却还要求他人也应该丧失提出尖锐问题能力的人们。重新评价“六四”是未来历史的必然,重新评价“六四”的过程应当是一个疗治我们整个民族病痛的过程。我们的痛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亲人被杀,更深层次的痛还在于我们,由于恐惧而将异常简单的是非判断问题异常地复杂化。我们民族要有勇气反思过去七年来,在中共残酷镇压和杀伐同样是我们亲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中,对是非判断如此简单的问题上,我们的全民族表现出的、直至今日的复杂的精神、心理状态。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无论是暴虐的惨烈程度,还是被杀戮及被迫害的人员的广众程度和持续性方面,尤以对整个社会的法律基础、资源及社会道德、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戕害程度,都绝不亚于“六四”事件。但在七年后的今天,西方世界已开始关注发生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令人怵目惊心的灾难实际,我们国内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死寂无声!这如何了得?我们说:这种麻木和沉默是成就中共杀戮暴行的绝对条件!这话可能又让一些同胞感到异常的刺耳!但我们都扪心自问,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我的中国同胞们,一位名家曾说过:“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被征服,还没有堕落,即她的处境还有改善的可能。幸运的机会一旦出现,这个民族就不会辜负这样的机会,但极权统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使她堕落,它使得这个民族习惯于践踏她自己过去所尊敬的东西,奉承她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这个民族的处境就很难获得改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的公义;作为一名律师,我一直致力谋求法律上的公平。对于“六四”屠杀,以及所有共产党的罪恶,我下定最大的决心,也愿我们民族的每一个同胞也能下最大的决心,只要这些罪恶没有得到法律和道德层面上的公平解决,我们就不让历史翻过这一页。
结果的公平,恰如其分的奖赏、惩罚和补偿,以及必要且绝不过分的宽恕,才会让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心服口服,才不会有未来的冤冤相报,我们的民族才能放下这浸满鲜血的包袱,没有遗憾地经由和解之门走向未来。寻求公平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的良知拷问过程,我们需要问自己为什么正义的到来如此之晚,我们的恐惧和懦弱起到了怎样的阻碍作用,给我们自己、他人乃至民族带来了怎样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这一过程也将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过程,我们不能彻底反思历史,就会让这样的罪恶再次发生。
《圣经》上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二书1:10~12),当一向渎神的中共肆意屠杀民众时,那些给中共请安的人,即使手上没有沾上看得见的鲜血,他们的灵魂也沾上了血污。
在这篇文字的最后,我想再次与我的中国同胞共勉:疗治“六四”伤痛,疗治我们民族伤痛的过程,不应是让凶手们再玩“平反”把戏;根绝民族病痛的方法,就是不再相信凶手,不再惧怕凶手,并彻底地抛弃凶手。
2006年6月7日 在有中共特务围堵的日子 于北京的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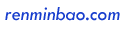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