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臺之初人員非常緊張,專業人員珍貴如鳳毛麟角。由於所有人都是義工,這裏的臺長只不過是對外聯絡和公關的頭銜,對內大家都是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則配合協調工作的。一位副臺長在回憶草創時的經歷說,他們有一次開電視臺的籌備會,他放眼一看周圍的志願者幾乎都是博士或教授,可惜都是什麼計算機系的教授、生物博士、化學博士、物理博士,幾乎沒有什麼專業人員,有管理經驗的也不多。但是大家都覺得創辦一個不受中共滲透、控制和威脅的華語電視臺,還世界華人以最起碼的知情權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再難也要做。沒有專業經驗,大家就花錢到外面去學。好在這些人都是學習高手,很快就掌握了必要的技能。
由於這些人都是義工,因此都面臨着一個解決生活來源的問題,所以他們只能白天象普通人一樣到公司去正常上班,下了班以後到電視臺工作。因爲沒有經驗,開始製作節目的效率很低,燈光設置、錄音、剪接都相當緩慢。一位叫楊帆的主播說起過當初的艱辛。
“2001年年底,我正式成爲電視臺的一員。在電視節目正式上衛星之前,我們有兩個多月的練習時間。這段時間中,我每天下了班就去電視臺,最早十二點半回家,一般都是一點多鐘。做圖像編輯的同修更辛苦,常常凌晨三、四點鐘才離開。大家第二天都要上班。
“我最先接受的培訓是發音和化妝。有搞專業的同修教化妝,看看桌上擺的那些化妝用品,沒有幾樣是我認識的,認識的也不清楚怎麼用。當然化妝只是其中的一項而已,還有頭髮、服裝、首飾、播音時的表情、播報的語氣、語速和抑揚頓挫。這方方面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是一個播音員呈現給觀衆的整體印象,主播的形象也是電視臺的形象。
“一天晚上,是我練習播音。我和圖像編輯合作,要像正式做新聞那樣練習。我從晚上八點坐到鏡頭前,練到凌晨十二點。回家的路上,我想:用4個小時應該能做出半個小時的新聞了吧?第二天,我問圖像編輯:『我們昨天晚上做了多長時間的新聞?』『十分鐘。』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問:『就做了十分鐘的新聞?』『是啊,就十分鐘。』回家的路上,我反覆的想着:4個小時,十分鐘。按這個比例,要想做半個小時的節目就得12個小時。我要是從晚上八點開始錄製,做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剛好九點鐘去上班。我覺得我可以做通宵,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這樣堅持多久。”
像楊帆這樣的疑問,也許當時電視臺人人都有。那時新唐人全球記者站還沒有成立起來,新聞來源主要是購買新聞社的報導,再翻譯成中文。新唐人每天至少要播報四次新聞,早上四點半就有一次。新聞主編凌晨兩點就不得不爬起來,跑到地下室去挑新聞稿件和鏡頭,另外有人將選中的新聞譯成中文,還需要主播、攝影師、配音和剪接等許多工作人員的配合,才能把新聞製作出來。也許一天只睡一兩個小時,偶爾爲之還沒有什麼,天天如此實在非常吃力。我在去電視臺的時候,常常會看到一些人靠在椅子上打盹兒。
爲了減輕電視臺的壓力,許多外地義工辭去了他們報酬豐厚的全職工作,到紐約去找工作,甚至只能做半工,以便就近支援新唐人。當時有個叫梅梅的主播是從佛羅里達搬過去的;金然是從亞特蘭大搬過去的;方菲原來在密西根的大通信公司工作,後來也搬到了紐約。新唐人的一位副總裁也從外州換到紐約附近的一所大學當教授。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讀碩士期間趕上暑假,就到電視幫忙臨時性地做主播,每天一大早去臺裏,晚上常常一點以後回到住的地方。爲了省錢,和大家擠住在曼哈頓上城的一間公寓裏,路上地鐵票和中午盒飯都是自己出錢,更不要說更昂貴的服裝和化妝品了。有的義工到臺裏做節目,從外地趕到紐約,單程開車要四個半小時,路上的過路費和汽油錢也都是自己負擔。做完節目已經是深夜,爲了節省住酒店的錢,再獨自開車往回趕,回到家裏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五、六點鐘了。做一週經濟節目的許佳盈等義工每到週五都是徹夜不眠趕製節目。
電視臺由於人手奇缺,很多不懂英文和計算機的老爸爸、老媽媽們也去幫忙。他們除了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力氣活兒之外,電視臺還把一些例行的「高科技」工作交給他們做。年輕的義工們給他們詳詳細細地列出一個流程寫在紙上,告訴他們在計算機上按完了這個鍵,然後按那個鍵,再用鼠標點什麼地方。實際上這些老爸爸老媽媽們根本就不認識屏幕上的英文菜單,就憑着硬記下這些流程來分擔年輕義工們的壓力。
2002年夏天的時候,電視臺因爲製作部和播出部份在兩處實在不方便,就在曼哈頓中城租下了現在這個辦公室。當時就像一間大倉庫一樣。很多老年義工和爲數較少的年輕人開始裝修這間大屋子,把它隔斷成播音室、化妝室、會客室、技術部、播出部、資料間等地方。新唐人的男女主播們,那時也會在播音的間隙跑過去搬大木板。
由於維持節目製作和播出的人員都奇缺,新唐人剛剛創臺期間更沒有精力和人員去跑廣告業務,最開始大半年的時間幾乎沒有什麼廣告。整個電視臺的運轉全靠個人捐款來維持。後來,臺灣因爲修煉法輪功的人有幾十萬,其中有一些學生,還有一些就是在臺灣大電視臺的專業人員,他們知道紐約的艱難後,或者在暑假期間、或者在休年假期間跑到紐約來支援,形勢才稍微緩解一些。
由於新唐人是二十四小時連續播出,節目來源開始時也很匱乏。一個綜合性的電視臺需要有娛樂節目、評論節目、生活節目、教學節目等等。外州的義工們就盡其所能地製作出這些電視節目來支援新唐人。
我認識一位林先生,是個法輪功學員,身在華府。從新唐人創臺之初就開始爲新唐人提供技術支援。他是一位電腦工程師,收入不錯,但是他幾乎把他全部的節餘都投放在法輪功的真相資料和新唐人電視臺的運營上,至今仍然一家三口擠在一個租來的兩居室公寓中。其中客廳設置了各種背景,用於拍攝幾個電視節目,一間臥室被改造成了工作間用於剪接。稍大的臥室連個像樣的床都沒有,只有兩個床墊子,一家三口睡在上面。整個公寓因爲堆着各種設備顯得十分擁擠。林先生爲人比較內向,每天除了自己製作專題片外,還有接不完的電話,回答各地義工遇到的技術問題。他常常悶頭幹活兒到凌晨三、四點鐘才睡,第二天早上還要繼續上班。因爲任務繁重,吃飯的時間也儘量壓縮,經常以麵條充飢。我每次到他家裏,常常想起孔子的一句話「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行而慎於言。」
一個電視臺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觀衆收看。從這一點來說,新唐人的發展也和中共對華文媒體的滲透有關。很多敏感話題關係到人們日常生活和社會大的發展走向,但是一般的華文媒體都不敢觸及,或做深入報導。這就等於把觀衆羣拱手讓給了新唐人。
像「江澤民出賣領土」、「六四」、「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地下基督教會被鎮壓」、「民間維權運動」、「SARS真相」,以及「法輪功」的議題都是大陸竭力封殺的。而新唐人卻總是在第一時間進行詳細追蹤報導。舉例來說,新唐人對於「SARS」的報導,比中共官方不得不承認SARS真相早了三個星期。新唐人新聞製作部的主任李國棟說,「如果新唐人的節目能夠在大陸自由播出,人們提早三個星期做好預防準備,恐怕不會危及到那麼多中國人的生命,甚至引起世界的恐慌。」
新唐人的記者站在世界各地也都慢慢建立起來,更逐步走進社區,這些記者站的設備都是義工自己購買的,人力更是分文不取。出去採訪的車馬費都是自掏腰包,包括和客戶一起吃飯的錢,也沒有一分是新唐人給的。
可以說,新唐人的廣告員也並不都是很專業的人員,大華府地區的一位廣告員就是學計算機的碩士。但是許多商家都是受到新唐人這種「鐵肩擔道義」的精神感召,開始在新唐人上做廣告。
一般人聽說新唐人在全球四大洲設有五十多個記者站,都非常吃驚,感覺每年花費至少要兩億美元。其實新唐人每年的花銷非常少,除了衛星租賃費用外就是紐約辦公室的租賃費用,而各地上有線電視和辦公室租賃都是各地自己花錢。很多地區的辦公室就是義工家裏的地下室。
中共經常在外面散播說,美國給了新唐人多少錢、臺灣給了新唐人多少錢,實際上新唐人除了廣告和個人捐款外,沒有拿任何一個政府或大企業的一分錢。作爲一個非盈利組織,新唐人的一切帳目都是公開的,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查。中共以傾國之力花錢做事,他們永遠也理解不了這羣完全憑着信仰和信念做事的人。
尤其令我感動的是新唐人電視臺的法輪功學員,他們被中共利用整個國家的宣傳資源、外交資源和特務資源造謠誣陷,國內的功友乃至親人被騷擾甚至虐待致死,本來他們應該是最需要別人幫助的。但是如今他們不但頂住了這些壓力與不幸,反而用他們與電視臺運營資金相比菲薄的收入和極爲有限的時間幫助支撐着這個電視臺的運轉。讓所有的華人能夠透過這個窗口了解對於他們來說也許是生死攸關的真相。
我個人對新唐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本文也必然忽略了很多更加感人的人和事,但我相信每一位參與新唐人創業的人,他們這段「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經歷都可以寫一本書。當我看到他們的處境時,也常常會想如果海外華人都能夠伸出援手,每一個人哪怕是隻提供最微小的一點點幫助,新唐人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艱難。如果我們都是在享受新唐人爲我們提供的自由資訊的窗口,難道我們對改善新唐人的處境會沒有道義上的責任嗎?
(大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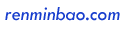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