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3點左右,他們停車請我吃米線權當午飯。一邊看着我吃,一邊嘻嘻笑着:「還是家鄉的米線好吃吧?以前每次回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找碗米線吃吃。」昆明的2月一片明媚春光,我卻毫無心緒,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個小販,打出「昭通涼粉」的牌子,不禁心中微動,想起趙昕。在派出所時,國保曾威脅過我:「我們已經特地派了一批人到昭通去了,現在估計應該到達。我們會向趙昕了解情況,如果他說的和你說的對不上號,那你要負全部責任。」我想,趙昕十有八九也失去自由了,於是對國保說:「我還想吃一碗涼粉,那邊有個賣涼粉的。」國保讓米線鋪的老闆娘要了碗涼粉來,我津津有味吃着,越發懷念我們在一起時自由的日子。無奈造化弄人,轉眼間皆已是南冠之客。
吃完涼粉,又接着喝碗裏的醋水,國保在一旁暗笑,大概笑我小氣饞癆症。昭通遠在800裏之外,無人可以傳遞音訊,只有吃一碗昭通的涼粉,暫與君別。於是戀戀不捨喝下最後一滴醋,復又上了國保的車,接受「監視居住」了。
我不明白,「監視居住」這個詞,究竟含義如何?在「居住」一詞前面加上「監視」二字,讓人老覺得不倫不類,無論文理還是法理,都說不過去,不知哪位漢語高手發明了這個詞。退一萬步講,既然是「監視」,那麼他們只能看我幹什麼,而不能限制我的自由。我一直試圖給他們改改,但總也改不好。這個詞就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一樣可笑,「國家」怎麼能用來做「政權」的定語?估計那幫發明這類詞彙的人,初中語文沒及格。
那地方名字似乎叫「鑫安會務中心」,後來得知,此地還有一個雅稱名爲「民工會務中心」。國保把法律文件給我看了後,又都拿走了,不給我留一份。然後兩位治安警察進入。我們三人無事,開始鬥牌作樂。到了吃晚飯光景,看管我的四個人正式到齊:兩名我的戶口所在地昆明經濟開發區分局的警察,兩名我的戶口所在單位昆明船舶集團保衛處幹部。
我們的日子大概這樣度過:早晨8點,服務員送來早餐,吃完早餐去健身器材上鍛鍊鍛鍊,然後回來鬥牌;中午12點服務員送來午餐,吃完午餐散步,散完步接着鬥牌;下午6點服務員送來晚餐,吃完晚餐散步,散完步他們看電視,我搬張桌子坐在馬桶蓋上寫作。帶隊的老同志不屑於鬥牌,熱衷於打電玩,帶了個PS2來玩。他是位電玩發燒友,據說癮比許多中學生還大。剛開始時宣稱:「只要有遊戲機打,我就永遠不會無聊。」但是才兩個星期,他就徹底厭煩了遊戲機,整天睡大覺,除了吃三頓飯,就是睡覺。睡了一個星期,又改看電視,堅持了一個星期。連我都不知道他後來是怎麼熬日子的。
當然,這是國保不來時的情景。如果國保來,那我就接受審查,他們各散虛空。國保開初大概兩三天來一次,後來日漸稀疏。
我們打壞了六副牌,一個月之後,一個看守說:「這一年的牌一個月全打完了,打牌打到想吐啊!」到了第五個星期,帶隊的老同志問:「小歐,你現在什麼感覺?」 我說:「很好啊!日子過得不錯。」他說:「我現在真的感覺是在坐牢。」想了一會,又說:「也好,先嚐嘗什麼滋味,等哪天我也落到你這般田地,也適應些。」
某天,一位看守問我:「小眼鏡啊!你的事要到什麼時候結束啊?」我說:「我怎麼知道啊?這事國保說了算,他們說了,監視居住,最長期限半年。」他大驚:「半年!我要發瘋!」我說:「半年很好啊!正好無牽無掛看世界盃。」
這裏緊靠滇池,出門就是水,我喜歡沿着滇池岸上的一條小路散步。初春,路兩旁新種的櫻花逐棵綻開,紅紅白白滿載憂傷。但是我最喜歡的一件事,還是獨處。每天晚上他們在屋裏看電視,我在衛生間裏寫作。衛生間窗臨滇池,夜來風高浪急。如果有月色,那我最爲心動。每晚都在對着黑暗的湖面,想念我的愛人。我寫了幾十首詩,有些還頗長。還有些散文,以及國保要我寫的材料。加起來大概有毛毛的九本信籤紙,用了八支油筆。
當初我準備買紙筆的時候,國保說早就給我準備好了,然後取出一支筆和一本信籤給我看。我一笑,買了十本信紙十支筆。國保譏誚:「買這麼多幹嘛?你又用不完?」到了後來,他們才知道我可不是瞎搞。要是沒那麼多羈絆,估計能寫50本,用掉50支筆。
日子難熬歸難熬,但日子還得過下去,當你無法改變生活狀態時,就只有去適應它。
起初,他們對我看守頗嚴,上級下了命令,每天夜裏得有一個人清醒着,防我自盡或逃跑。我們五個人,兩個房間四張床。我佔掉一張床,帶隊的老同志佔掉一張。剩下三人輪流值夜。一個禮拜後,他們不再坐在椅子上熬夜,而是靠在椅子上睡覺。兩個禮拜後,他們弄了些座墊進來打地鋪。我說:「今晚我睡地鋪吧,我們輪流睡地鋪。」他們說:「你老人家可是大熊貓,國寶級的,哪能讓你老人家睡地鋪,我們兄弟幾個的職責,就是把你老人家伺候得舒服了。」
第二天,我們正在鬥牌,透過玻璃窗遠遠看見國保的車開了過來。我說:「國保來了。」他們說:「國保審國寶來了。」我們的牌局正進行到關鍵處,大大地敗興。
每次和國保搞完,都要生一肚子氣。因爲國保口口聲聲說要請我吃飯,卻到最後都沒兌現過。而他們,卻三天兩頭跑來蹭飯吃。
有一天,國保要我寫寫幾個所認識的幾個異議人士之思想狀況。我覺得,異議人士們不外乎是些自由主義者外加些基督徒。於是將自由主義思想的精髓介紹介紹,然後和馬克思主義對比對比。又介紹介紹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他們似乎對此頗爲不滿,認爲自由主義和基督教都是西方的東西,是敵對國家傳來的。我奇怪,他們的共產主義,難道不也是起源於敵對國家嗎?他們提醒我,美國佬想搞和平演變全盤西化。我更疑惑,和平演變總比共產主義的暴力演變好吧?至少不用打仗死那麼多人。而且,不是早就全盤都被共產主義化了嗎?難道共產主義不是西方的東西?
國保們苦口婆心勸我,老祖宗的東西就是比西方好。我更奇怪,老祖宗要女人裹小腳,要三拜九叩,他們怎麼不復興這些偉大中華傳統啊?老祖宗只有朝廷、衙門,又沒人大、政協、公檢法,更沒有市場經濟。老祖宗說:君子不黨。那既然他們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比君子更進一步,更不應該搞什麼黨了,還搞得那麼大,比牛屎也小不了多少。老祖宗還說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爲什麼他們要養那麼多女子與小人?
總之,國保讓我別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中國的文化要學習,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五千年文明……我說:打住!請問五千年從什麼時候算起?國保啞口,然後給他們講講歷史和學術,告訴他們文明的開端從文字的出現算起,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所以中國文明最多有三千五百年。連老祖宗有多少年的文明都不知道,還來教訓我不知道老祖宗的文化?然後我給他們講講管仲和孟子關於顛覆政權的觀點。
當然啦,和國保在一起也並非沒有好處,我可以撈到十塊錢一包的好煙抽,想抽就大搖大擺自己拿他們的煙抽。一邊抽一邊說:「趁有煙,趕緊抽,過幾天進了看守所,就沒得抽咯。」
有一天國保問我:「你最近,有什麼想法?」我說:「有啊!我得好好想想,怎麼才能養得白白胖胖地,積攢些膘水,省得進了看守所變掉毛狗。」他們說:「不會這麼簡單吧,發生了這些事,總是要有很多想法,要反思的嘛?」我大笑:「庸人自饒,要那麼多想法幹嘛,又不能當飯吃,眼前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養膘,其它都靠邊站去。所以我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啊!」他們又問:「吃了睡,睡了吃,那不成了豬了嘛?這可不是你的作風?」我說:「我就是豬啊!養肥了好讓你們來殺嘛。哪家殺豬,不得先養得圓乎乎的才捨得殺?」
終於國保通知我,要將我送回老家,說是我吃他們喝他們,他們受不了了,要吃自個回家吃去。那時我頭髮已經長的象豬窩,便請警察帶我到賓館外理個髮。恢復了精精神神的小平頭,等着回家見媽媽。
這個春天,來得不合時宜,去得倒是蠻實在。
轉自《民主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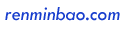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