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妮是教體操的,身體非常健康─至少表面看上去是這樣。她愛好運動,最喜歡的運動是踢足球。所以,每次到診所來時,她身體上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從腳扭傷到膝蓋踢傷,總是這裏還沒好那裏又傷了。
有一次我回家路過簡妮踢球的那個足球場,就決定站在柵欄外觀看她踢球。簡妮那身醒目的衣衫一下子就讓人認出她來了。今天她是守門員,只見她向足球撲過去的時候,那衝出去的速度就象一枚發射出的炮彈一樣,快的令人難以想象。她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將自己的身體毫無保留的拋射出去,我看得驚呆了。
當她看到我向她豎起大拇指時,也興奮地歡呼起來,快樂得象孩子一樣。
當她再來我的診所治療時,我表示了對她在球場上的勇敢的敬佩。我很難想象如果這球是對我飛過來的話,我會是個什麼狼狽樣。
「我踢足球時,經常會想到那球是我的繼父。如果20多年前我有今天這個體力,他決不敢靠近我。可惜我那時太弱了。如果不是母親還活着,我早就把他送進監獄了!」她的語氣中充滿了仇恨,讓人感覺到這怨恨深深地埋在她的心底永遠難以抹去。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他們再碰到一起,會是什麼情形。
「你的癲癇病是從家族的哪一方遺傳來的呢?」我問。
「母親,祖母那兒。」她憂鬱起來。「兒童時,當我受到欺侮和虐待時,我就巴不得自己犯病。後來,我甚至能夠控制自己想什麼時候發作就什麼時候發作。那是爲了保護自己,但後果卻是我沒有預料的:我變得愈來愈弱,最後連走路都困難了。」
「那你母親知道嗎?」我問她。
“母親是知道這一切的。因爲我還有其他的姐妹,爲了保護她們,我就成了犧牲品。母親自己也經常被他打得鼻青臉腫。母親與其說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不如說是個佛教徒更合適。她相信宿命論,她總是說:『我們上輩子做了不好的事才得到這樣的報應。你繼父雖然對你不好,但畢竟桌上的麵包是他提供的。沒有他,我們就要去要飯了,就因爲此,我們要忍受。……』
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我就知道人間的一切都不是免費的,都要付出代價的。爲了桌上的麵包,全家人不出去要飯,我要付出。但是我繼父也是要爲自己的行爲付出代價的。將來會有一天我和他站在上帝面前,不用我說一句話,當上帝看到他那墮落的靈魂時,立即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將他打入地獄裏去……”
簡妮除了癲癇外,還患有嚴重的憂鬱症。她因長期失眠或惡夢不斷,靠藥物來維持。她的情緒起伏很大,再加上精神緊張,使她周圍與她一起生活和工作的親人、朋友、同事都無所適從。她過度敏感,總感到別人的話中帶刺,含沙射影。僅有極少數知道她的童年遭遇的朋友,才能諒解她這古怪的性格。儘管她努力想改變,但因爲這童年創傷的烙印實在太深了,使她無法擺脫,生活得惶恐不安。
在西方國家,心理醫生除了給病人治療精神的藥物,傾聽病人的訴說,有時還會教給病人一些解除病人症狀的練習方法,比如捶枕頭髮泄心中的憤恨,到無人的地方大喊大叫把心裏埋藏的悲傷釋放出來,等等。
簡妮的心理醫生爲了使她能夠徹底的擺脫繼父對她心靈上的創傷,就專門選定了一個日子開了一個她繼父的「追悼會」,儘管他還活的。追悼會的形式與一個真人死去是完全一樣的:請來她的朋友、同事,靈堂放着蓋了蓋子的棺材,一切都和真的一樣齊全。其目的是爲了讓簡妮把她繼父從記憶中永遠抹去。在追悼會上,簡妮讀了長長的悼詞,從各個方面痛斥了繼父一番。當時她感覺這個人終於從自己的心底徹底地挖了出去,被永遠地埋葬了。
可命運似乎在同簡妮開玩笑。她的丈夫,那個與她朝夕相處的人,除了模樣以外,其它的地方包括講話、習慣、愛好,甚至連放工具的順序都與她的繼父極其相像。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過去每到星期五,她的繼父規定家裏人只能吃魚,爲了抗拒,簡妮一生中對魚是碰也不碰的。而簡妮的先生馬克一到星期五不是要在家裏吃沙丁魚就是偷偷的跑出去吃魚。別的時候,他倒不那麼固執。因此,每到星期五,家裏氣氛就緊張,烏雲密佈……
爲了給她治療,我請她「星期五」來我的診所。可是她一次一次藉口推脫:一會兒車鑰匙不見了,一會兒孩子病了,多少次的失約,就是無法來到我這兒。我耐心地等着。
終於有一次,她在星期五來了,又是悲傷又是氣恨,她告訴我她跟先生已經幾天不說話了。她問我:「難道我這一生中永遠也擺脫不了這個陰影嗎?」
「什麼陰影?」我問。
「這星期五吃魚的惡習。現在連孩子都願意吃,我愈是反對,他們愈要吃。」
「星期五吃魚有什麼問題嗎?那許多人家住在海邊就拿魚做食物呢。」我說。
「唉,你知道,我一想到那是我繼父的規定,就……」
「簡妮,是到寬宏大量的時候了。你因爲在自己的童年受過欺侮,就用這種方式讓所有你身邊與這歷史不相干的人一起承擔這後果。你這麼苛刻地要求別人,現在連孩子都不願意了。他們有錯嗎?你吃過苦,更應該懂得怎樣爲別人着想,愛護家人,使他們生活得更好,不再受自己受過的苦。俗話說,給別人一丈地,自己也會得到一丈地;給別人尊重,自己也會得到尊重。你說對嗎?」
她看着我沒有回答,陷入沉思……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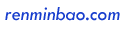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